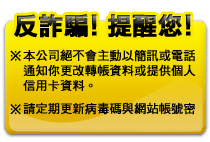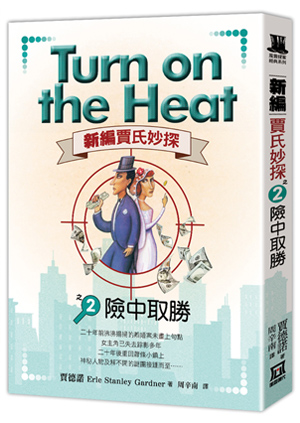
我推開漆著「柯氏私家偵探社」的門,卜愛茜自速記本上抬頭望我,兩隻手仍不停在敲打字機字盤,她說:「進去,她在等你。」
快速斷續的打字聲,雜著我的腳步聲,經過辦公室,經過漆著「柯白莎──私人辦公室」的門。
身材巨大,穿著庸俗,常處於好戰狀態的柯白莎,像隻牛頭狗似的坐在辦公桌後面。看得出她在裝腔作勢地翻動面前桌上的文件,手指上的鑽石也不斷在窗外射入的陽光中閃爍著反光。她對面,坐在顧客椅子中的是四十出頭的一個瘦個子。他用怕事又急於辦事的眼光看向我。
柯白莎說:「賴唐諾。怎麼要那麼久才到?」
我不理她,直接觀察我們的顧客,他是個灰髮瘦子,八字鬍也是灰的,但修剪十分整潔、他嘴唇的型態顯示他很有決斷力。和焦慮的外型不相吻合。他戴了一付深色鏡片的眼鏡,我看不出他眼睛的顏色。
柯白莎接下去說:「王先生,這位是賴唐諾,就是我介紹過他給你的。唐諾,這位是王先生。」
我鞠躬如儀。
王先生控制自己,用有教養,要別人覺得他存在的聲音說。「早安,賴先生。」他沒有把手伸出來。他的樣子看來有點失望。
柯白莎說。「千萬別被唐諾的外型騙了。他是個非常精明能幹的人。他天生沒有肌肉,但是他有頭腦。他是變種。越打擊就鬥志越高,他懂得該怎麼做。王先生,不必擔心。」
王先生點點頭,我看得出有點勉強。我仍看不到他的眼睛。
柯白莎說:「唐諾,坐下來談。」
我坐在那張硬板直背椅上。
柯白莎對王先生說:「有人能找到她,唐諾就也可以。他比外表要老成多了。他本是個律師,他被律師界趕出來,因為他告訴一位顧客如何可以合法謀殺。唐諾自以為只是討論法律漏洞,但是公會認為那是漠視神聖。當時他們認為不合理,也不會成功。」柯白莎停住,喀喀地笑出聲,又繼續道:「唐諾到我這裡來工作,第一件案子就表演給大家看,我國的謀殺案處理過程中的確有一個大漏洞在。任何人都可以謀殺了人而不受處分。現在他們在修改法律。這個唐諾就是我要介紹給你,替你辦這件案子的唐諾。」
白莎用一個裝出來的笑容向我這邊一看,笑了等於沒有笑。
王先生點點頭。柯白莎說:「唐諾,在一九一八年,有位林吉梅醫生和他太太住在橡景,栗樹街四一九號。發生了醜聞,林家開溜了。我們不在乎男的去那裡,替我把林太太找出來。」
「她還在橡景嗎?」我問。
「沒有人知道。」
「有親戚嗎?」
「沒聽說過有。」
「她失蹤時,她和她丈夫結婚幾年啦?」
白莎望向王先生,王先生搖頭。
柯白莎繼續看著他,最後他用一貫的形態,像是他特徵似的學術派頭說:「我不知道。」
白莎對我說:「有一點你給我記住,我們並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在查這件案子。再說,我們僱主是什麼人,更需要保密。你可以把公司車開出去。現在就去,今天再晚也要到橡景。」
我看向王先生說:「我一定得多知道一些。」
王先生說:「沒有問題。」
白莎說:「假裝她的遠親。」
「她幾歲了?」我問。
王先生蹙起眉頭。他說:「我不是真正的知道,到了那邊你問得出來的。」
「有孩子嗎?」
「沒有。」
我看向白莎。她打開辦公桌抽屜,取出一隻鑰匙把現金盒打開,交給我五十元。「省著點用,唐諾。」她說:「很可能是長期追蹤。計算每一項開支,可以追得遠些。」
王先生把手指交叉,把雙手放在雙排扣上衣前,他說:「說得有理。」
「有什麼線索可以優先偵查嗎?」我問。
白莎問:「你還想知道什麼?」
「所有可以得到的資料。」我說,眼睛可是望向王先生的。
他搖搖頭。
「她的背景如何?受過工作的訓練嗎?她做過什麼工作?有些什麼朋友,自己有錢嗎?她是高是矮,胖還是瘦,金髮還是黑髮?」
王先生說。「對不起,幫不上你忙。」
「假如找到她,我怎麼辦?」我問。
「通知我。」白莎說。
我把五十元放進口袋,把椅子推向後面。我說:「王先生,幸會。」我逕自走了出去。
經過辦公室時,卜愛茜都懶得自打字機上抬頭。
公司車是一部老傢伙,輪胎快要磨到鋼圈了。散熱器漏水。只要超過五十英哩,兩隻前胎就猛跳扭扭舞。引擎不斷咳嗽,像是隨時要淹死。今天天氣真熱,向山上爬簡直是苦不堪言。山谷中氣候更熱,我兩隻眼睛漲得像煮熟了的雞蛋,要不是有眼眶在前面,它們早就跳出來涼快了。我尚還不致餓到值得停車,所以半路買了個漢堡就又上路,一手用來吃,一手在開車。晚上十點半我來到橡景。
橡景是建在山腳下的一個鎮,這裡氣候涼快,大氣中的濕度高,有蚊子。一條小河自山中蜿蜒而下,經過本鎮散佈到下面的平原去。
橡景本身是個過氣的小鎮,九點以後沒有市面。街上房子都是老的,替街道遮蔭的大樹都是老的。城市本身發展不夠快速,即使有心的人也無法據此擴大街道和鋸掉兩旁的大樹。
皇家大旅社的門仍舊開著,我進去要了一個房間。
從窗口裡照進來的晨陽吵醒了我。我梳理,穿衣。自窗口對本鎮來個鳥瞰。我看到二十世紀極早年代式建築的法院。自大樹頂上望出去可以見到河流下游的一瞥,向下望可以見到一條巷子,兩旁堆滿了用過的木箱、紙箱和垃圾筒。
我出去找找看什麼地方可以吃早餐,找到一家門外聞起來香噴噴的餐廳,裡面有點剩菜味,並且油膩膩。吃完早餐,我坐在法院梯階上等候九點鐘上班時間的來到。
鎮公所的職員悠閒地姍姍而至。大多數是臉上缺乏表情的老人。他們選樹蔭多的地方走,只要有人提任何一點資料,都可以停下來閒聊。看到我坐在門等候,經過我身旁時都好奇地看著我。他們知道我不是本地人,也表露出知道我是外地人。
大廈裡一位臉上有稜有角的女公務員瞪著黯淡無光,黑漆漆的眼珠子聽我說完我的請求,遞給我一本紙封面一九一八年戶籍的登記本子。本子裡面的紙頁早已變了黃色了。
在八畫的部分我找到了林吉梅,職業是醫生,地址是栗樹街四一九號,年齡三十三。同頁登記的是林亞美,家庭主婦,栗樹街四一九號。林亞美沒有登記年齡。
我要求著看一九一九年的登記本。裡面沒有這兩個人的名字。我走出大樓的時候,感覺到人們都在背後看我。
本鎮只有一家報紙,叫「舌鋒報」,自報館漆在窗上的字眼看得出是一週出一次。我走過去,在櫃檯上輕輕敲幾下。
打字的聲音停止,一位赤褐色頭髮棕色眼珠雪白牙齒的小姐自後面隔間的部分出來,問我有什麼事。我說兩件事請她幫忙。一是一九一八年的舊報,另一是鎮上那家餐館可以吃一頓好的中飯。
「有沒有試過尹記?」她問。
「早餐就是在那裡。」
她說:「嘎!」過了一下她說:「那麼試一下古家館,再不然就只有皇家大旅社的餐廳。你是說一九一八的舊報?」
我點點頭。
我沒有再看到她潔白的牙齒,因為她把兩片嘴唇閉得緊緊的。連棕色的眼珠也不再發亮了。她想說點什麼,自己立即改變了意見,走進後面的房間裡去,過不多久,拿出一疊用兩條木條夾著的舊報。「有什麼特別要的資料嗎?」她問。
我說:「沒有。」就開始自那年元月一日看起。我很快看過一兩版,問道:「你這個不是說是週報嗎?」
「現在是週報,不過在一九一八年,我們是日報。」
「為什麼越變越差了?」我問。
她說:「這在我來之前。」
我坐下翻報紙。頭版都是戰爭消息,報告不少德國潛艇活動。有不少宣傳資料,說德國人砍男人手和女人乳房之類。國難公債各地推銷是有配額的,橡景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很多愛國的人發表言論。有一位受傷退伍的加拿大人來這裡巡迴演講。鈔票的流向都是往歐洲的。
我希望我要查的事夠資格上頭版。一九一八年的頭版,沒有提起。
我問小姐能不能暫時把一九一八年的留下,再借一九一九年的先看一下。
女的不吭一聲,只是把一九一九年的舊報紙交給我。我就看一九一九年的頭版新聞。休戰文告已發表,美國在文告中是救世主。美金、美國兵、美國文化離開歐洲,會有一個國家級的政治團體產生,據說可以扶弱抗強。以終止佔據永遠不會發生。全地球都會是和平民主。比較次要的新聞開始在頭版出現。
我在七月分的舊報找到了我要的消息。在頭條新聞裡這樣寫著「橡景名人欲訴離婚──林醫生宣稱精神虐待。」
報紙對要報導的內容是十分小心的。主要是登原告的訴訟內容。卜華律師事務所代表原告。報導說林醫生是整型科專家,林太太是年輕一代社會的領導人。兩人都是鎮上人人愛戴的人。兩人對「舌鋒報」記者都不肯發表意見。林醫生請記者去訪問他律師,林太太則說她只有在法庭才肯開口。
十天後林醫生的案子占了頭版全頁。「林太太指明關係人──社團領導人控告丈夫的護士」。
自報導中得知林太太應紀法官的查問,出面作證並控告了她丈夫的護士果薇安。說她是本案的關係人。
林醫生拒絕作答。果女士已離開本鎮。電話追蹤也未能成功。文中提起本案的歷史背景。林醫生在實習的時候,果薇安就是同醫院的護士。林醫生在橡景一開診所就請她到診所來,她便變成診所的護士。據報紙報導一部分林醫生的朋友來訪時都是由她接待,這些人對她非常支持,都肯作證指出林太太控告中指果女士的事,是荒謬可笑、無中生有的。
第二天舌鋒報說:紀法官簽發了要果薇安和林醫生出庭以便瞭解案情;發現林醫生因業務出鎮去了,完全聯絡不上;果薇安則尚未回來。
文後尚有花邊新聞,說紀法官認為果女士和林醫生是故意蔑視法庭的傳票。卜華法律事務所的卜律師和華律師則堅決的加以否認。他們說這種指責會造成社會視聽錯覺,對當事人發生偏見。他們說已經儘快在聯絡,不久即可回來作證的。
自此之後案情發展移到比較不重要的版面去了。一個月內和解契約登記生效。所有林醫生的財產全部歸林太太。但是她始終否認有什麼財務上的妥協。雙方律師也否認知道這種事。又一個月後,一位賴醫生自林太太手中買下了林醫生的診所和設備開始營業。卜華律師事務所除了仍說林醫生會自己回來向大家交待清楚外,其他一律閉口不談。
再向下的舊報已經不提這件事了。櫃檯後坐在高凳上的女郎看我翻這些報紙。
她說:「再向下不會有這件事的消息了。不過你看十二月二日的。當地花邊新聞欄還有一段。」
我把報紙向邊上一推,我說:「你知道我在找什麼?」
她看向我說:「你自己該知道呀。」
「是的。」
她說:「那麼最後一段也該看一下呀。」
一個粗嘎的男人聲音自隔間後在叫:「瑪麗。」
她自高凳溜下,走向隔間。低沉的聲音在咕嚕,過了一下女的回答他一兩個字。我回顧那疊舊報,把舊報翻到十二月二日。在花邊新聞中我看到林吉梅太太亞美準備到東方去和親友共渡聖誕,所以她要乘火車去舊金山,然後乘船經運河東行。當記者問她離婚案進行到了什麼程度時她說這件事已經全部交由律師處理,她自己連丈夫現在在什麼地方也沒興趣去管。這件事識者都認為無稽和猜說,謠言說非但她知道林醫生現在在那裡,並且她正準備要去和他重聚。
我等候小姐回來。她遲遲未出現。我走向街角的藥房,拿電話簿找律師欄。沒有姓紀的律師,沒有姓卜的律師、不過有一位華福侖律師,他的事務所在第一國家銀行大樓。
我選了沒有陽光直曬一邊的人行道走了兩條街的距離。爬上老房子搖搖欲墜的樓梯。走過不太水平的走道。我在一張亂拋著法律書籍的桌子後見到了華律師,他雙腳擱在書桌上,煙斗在他嘴裡。
我說:「我是賴唐諾。我想請教些問題。你還記不記得當時卜華事務所接手過一件林家夫婦的……」
「記得。」他說。
「不知你能否告訴我,林太太現在在哪裡?」我問。
「不能。」
我想到白莎對我的指示,決心自己冒點險。
「林醫生在哪裡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