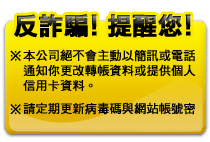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所謂女黑俠木蘭花、穆秀珍,全是無中生有,小說家製造出來的人物──」穆秀珍的聲音顯然是因為憤怒,而聽來十分尖銳,她手中拿著報紙,望著報上的一段文字,望到這裡,略停了一停,揮著手,用力在報上拍了一下,再提高了聲音,道:「蘭花姐,你看看,這是什麼話?太豈有此理了!」
為了加重語氣,穆秀珍在說完之後,還重重地「哼」了一聲。
木蘭花和安妮好像都沒有什麼反應,她們手上都拿著一本書,舒服地靠在沙發上,看得十分入神。
穆秀珍仍然瞪著眼,在等著木蘭花和安妮的反應,可是木蘭花翻過了一頁書,安妮也翻過了一頁書,兩人就像是完全未曾聽到穆秀珍剛才所讀的那一段報上的文字一樣。
穆秀珍又用力拍了一下報紙,陡然之間,大喝了一聲,道:「喂!」
安妮放下了手中的書。站起身來,木蘭花卻仍然一動也不動,安妮抬起頭來,笑著道:「秀珍姐,你在學張飛,要喝斷長板橋麼?」
穆秀珍神情憤然,道:「你們兩個,也太麻木不仁了,人家在報上這樣說我們,你們一點也不在乎!」
安妮側轉過頭向木蘭花看去,木蘭花並沒有抬起頭來,但是她卻知道安妮在望著她,她微微一笑,道:「秀珍好像要推翻言論自由的原則!」
安妮跟著笑了起來,穆秀珍鼓著腮,重重坐了下來。
寒流正侵襲這個城市,郊外,朔風呼號,尤其當天色黑下來之後,風聲吹過樹梢,發出尖銳的呼嘯聲,不過室內很溫暖,枯枝在壁爐中,發出熊熊的火燄,醉人的香味,和劈劈拍拍的聲響。
高翔到巴黎國際刑警的總部,去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反毒品計劃工作,雲四風和雲五風兄弟,則在北歐參加一個巨大的原子反應爐的建設工作,穆秀珍覺得自己家中太冷清,所以也搬了來,她們三個人像以前那樣,聚在一起。
不過,木蘭花和安妮兩人只顧看書,報紙上又有攻擊她們的文字,穆秀珍顯得很不高興。
她坐下來之後不久,又站了起來,道:「安妮,我們來下棋!」
安妮掠了掠髮,搖著頭道:「秀珍姐,我不上妳當了,你從來也沒有耐性下完一局棋的!」
穆秀珍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搭訕著道:「你們在看什麼?」
安妮揚了揚手中的書,書的紙張已經很黃,顯然已有相當的歷史,道:「太奇妙了,這是一部奇書,由著名的探險家、旅行家,安東尼博士手寫的!」
穆秀珍「哼」地一聲,道:「這個蘇格蘭人,已經逝世十多年了!」
安妮糾正穆秀珍的話道:「失蹤!」
穆秀珍瞪大了眼,提高聲音:道:「別和我爭,一個人失蹤了十多年,就算在法律上,也認為他已經死亡了,我說他死了十多年,有什麼不對?」
安妮是和穆秀珍爭論慣了的,雖然穆秀珍擺出一副嚇人的神態來,但是安妮一點也沒有給她嚇倒,仍是侃侃而談,道:「秀珍姐,你這樣說,有幾個漏洞。第一,就算他死了,也不一定是他失蹤那一天死的,所以,一個人失蹤了十多年,絕不等於他死了十多年,他可能是死了十年,甚至不到十年。第二,法律上認為一個人已經死亡,不等於這個人已經真正死亡了!」
穆秀珍瞪著眼,她給安妮的一輪辯駁,駁得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呆了半晌,才又好笑地道:「你這小鬼頭,嘴越來越刁了!」
木蘭花直到這時,才抬起頭來,微笑著說道:「秀珍,你的話等於是說,安妮在思想上越來越成熟了,你卻一點也沒有進步!」
穆秀珍「哇」地一聲,叫了起來,道:「你們兩個,是不是想打架?」
安妮和木蘭花一起笑了起來,安妮跳了起來,抱住了穆秀珍,穆秀珍也大聲笑著,兩個人一起滾跌在沙發上,客廳裡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穆秀珍翻了一個身,伸手拿起安妮剛才看的那本書來,木蘭花立時道:「小心點,書沒有出版過,是手抄本,十分珍貴,要是弄壞了,沒有法子賠還給人家!」
穆秀珍撇了撇嘴,向書的封面看了一看,一看之下,她就叫了起來,道:「難怪你們看得那麼入神,原來這本書那麼有趣!」
穆秀珍看到的書名是《世界上不可解釋的奇事》,這樣的書名,當然是會引起穆秀珍的興趣的。
安妮接替道:「當然,不然我和蘭花姐不會看得那麼入神,這部書,上下兩冊,一共記載了二十七種不可思議的奇事!」
穆秀珍迅速地翻著書,可是,她顯然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只是一面翻,一面迫不及待地問道:「在這二十七件怪事之中,哪一件最有趣?」
木蘭花不以為然地搖著頭,秀珍就是那麼心急,最好自己一點腦筋也不必動,就可以知道世上的一切。
安妮道:「我還沒有看完,但是我覺得他記載的,澳洲中部沙漠中的那件事,真玄妙到不可思議!」
穆秀珍瞪大了眼道:「怎麼樣的?」
安妮道:「有一隊汽車隊,在一九三○年,組織橫越澳洲中部的大沙漠,他們有著當時最好的裝配,一直和一家電視台有聯絡,報導他們的行蹤,可是在一天晚上,連人帶車,完全失蹤了!」
穆秀珍呆了一呆,說道:「那也不算什麼,在沙漠中,本來就充滿了死亡陷阱的!」
安妮搖頭,道:「不是,他們一共有八十四個人,四輛大卡車和七輛吉普車,可是全不見了,在無線電聯絡中斷之後,直升機和飛機的搜索持續了十五天之久,可是一點線索也沒有,而在他們失蹤的那一天,沒有氣候突變的記錄,沒有旋風,沒有沙漠變動的記錄,什麼意外也沒有,他們就消失了!」
穆秀珍搖著頭,陡地站了起來,道:「真有趣,我們到沙漠去看看!」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已經十多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沿著這隊汽車隊的路線,再進行探險,安東尼教授也曾走過一次,可是其餘所有的人,從雪梨到達爾文港,穿過了沙漠,卻什麼事也沒有!」
穆秀珍卻仍然固執地道:「或許我們再去一次,可以找到點頭緒來的,反正我們閒著,沒有什麼事!」
木蘭花搖著頭道:「你只不過是因為自己閒著,並不是真的對這件事有興趣!」
穆秀珍睜大了眼,木蘭花的神情忽然之間,變得陷入了沉思之中,拍著她手中的書,道:「而且,事實上,比較起來,這一件無風自動的事情,更加玄妙不可思議得多了!」
穆秀珍和安妮同時開口問道:「無風自動?」
木蘭花道:「是的,無風自動,我已經將安東尼教授記載的一切讀了好幾遍,而且,更神秘的是:安東尼教授就是為了探索這件不可思議的事,而突然失蹤!」
安妮和穆秀珍兩人反倒不出聲了。
她們和木蘭花在一起那麼久,自然知道木蘭花的脾氣,她們知道木蘭花絕不會無緣無故,對一件事表示那麼濃厚的興趣的。
而當木蘭花對一件事表示如此濃烈的興趣之際,那就是說:木蘭花已經決定要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她將會有所行動了!
連安妮也不知道安東尼教授記載的「無風自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既然安東尼教授是因為這件事而失蹤的,那麼,這件事必然有一定的危險性,那是一定的了,而如今,這件事可以說和她們都有了關係,穆秀珍雖然心急,也可以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她也不出聲,只是望定了木蘭花。
木蘭花略停了一停,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和日本軍隊,在緬甸北部的叢林之中,曾經展開過慘烈的爭鬥,有一天,發現了一座寺院──」
木蘭花略頓了一頓,才繼續道:「在這裡,安東尼教授記載得很模糊,他沒有記下準確的日期和地點,安東尼教授並不是那麼粗心的人,這座寺院被發現的日期,他可能沒有去查,可是地點,我看原來可能有一張地圖,但已經被人撕去了!」
木蘭花翻著書,指著書縫中的一頁,誰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那裡有一頁被撕去了。
木蘭花解釋道:「既然被撕去了一頁。但是剩下來的前頁和後頁,文字仍然是連貫的,所以我猜想那是一幅插圖──最大的可能是地圖!」
穆秀珍終於忍不住了,她用幾乎是哀求的語調道:「蘭花姐,你快說吧,那座寺院怎麼了?自己會動?」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是整座寺院會動,你別心急,要是你不耐煩聽我從頭講起,你可以自己去看!」
安妮說道:「蘭花姐,你說!」
穆秀珍拉過了兩隻墊子,拋了一隻給安妮,兩人一起在木蘭花的面前坐了下來。
木蘭花道:「根據安東尼教授的記載,當時發生戰鬥的雙方,一方是英國軍隊,指揮官是戴維斯少校,另一方是日本南進兵團中著名的驍勇善戰部隊,指揮官是平瀨榮作大佐,事後,英國以壓倒性的炮火取得了勝利。俘虜了平瀨大佐以下的官兵三百餘人,這是一場極其慘烈的叢林戰。」
穆秀珍雖然沒有再插嘴,可是在木蘭花講那一段話之間──她一共擠了五次眼,咳嗽了九次之多。
木蘭花並不理會她,繼續道:「那個叢林地區,一向外人罕至,是撣邦族的活動地區,也有一個小小的村落,不過日軍進攻在先,駐在那裡,戴維斯少校是奉命進攻的,目的是在於打通緬北和中國邊界的交通──」
這時,不但穆秀珍有點忍不住了,連安妮也咳嗽了幾次,木蘭花笑了起來,掩上了書,道:「好吧,既然你們那麼心急,我就將事情說得簡單一點,那座寺院,有一口極大的銅鐘,那口大銅鐘,每隔七年的一個晚上,會突然自己搖動,發出巨大聲響,連續約莫十分鐘之久才停止!」
穆秀珍「哼」地一聲,道:「不用說,那一定是撣邦族的土人在搗鬼!」
木蘭花笑道:「安東尼教授的看法,顯然和你不同,他為了要研究這件事,所以在每七年一次,那口巨鐘自己會搖動發出聲響的時候,事先去等著,來探究原因,而他一去就沒有回來,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的事!」
穆秀珍對這個日子,並沒有給予什麼注意,可是,安妮卻「啊」地一聲,道:「七年一次,還有十天,那口大鐘又該響了!」
穆秀珍聳了聳肩,道:「那又怎麼樣?難道我們也像安東尼教授一樣,去等著那口鐘搖動麼?」
穆秀珍只不過隨便說說,可是令她料不到的是,木蘭花竟然立即道:「是!」
穆秀珍「啊」地一聲。
安妮卻微笑著。
穆秀珍沒有料到木蘭花已有這樣的決定,但是安妮卻是早已料到的了。
由於木蘭花的回答,使穆秀珍感到擔憂、意外,所以一時之間,穆秀珍伸手指著木蘭花,張著口,卻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穆秀珍還沒有出聲,木蘭花卻又突然地道:「我們的客人來了,真準時!」
安妮揚了揚眉,她沒有聽到什麼聲響,也不知道木蘭花已經約了人,但是木蘭花既然那麼說,那就一定有人來了,她毫不猶豫地站起身,向門走去。
她來到門口,門鈴聲已經傳來,她打開了門,走進門外的小花園,看到花園的鐵門外,站著一個身形相當高大的中年人。
安妮一面向鐵門走去,一面就著門柱旁的燈,打量著她們的客人,同時在猜測著來客的身分。
來客的身形很高,身子很挺直,一件貼身的灰呢大衣,並沒有戴帽子,面色紅潤,大約五十五歲,很明顯的,是一個英國人,而且從他站立著的那種挺直的姿態來看,毫無疑問,他曾經是一個軍人。
安妮的心急速地轉著念,等到她來到了門口,拉開鐵門的時候,她的思索已然有了答案。所以她一面拉開門,一面已然客氣地說道:「戴維斯少校請進來!」
站在門外的英國人揚起了眉,現出了一種訝異而又有點憤怒的神情來,這時,木蘭花和穆秀珍也已經走了出來,英國人一面走進來,一面用宏亮的聲音道:「木蘭花小姐,我以為我們之間的約定,是有效的!」
木蘭花微笑著,道:「你說得對,事實上,我並未將你今晚來的事,告訴過任何人!」
英國人不相信地瞪了安妮一眼,道:「可是她──」
木蘭花一面向前走來,一面仍然帶著微笑,道:「這位是我的小妹妹安妮,我剛在和她們講述那座寺院被發現的情形,你的身分和名字,我想是她自己想出來的,是不是,安妮?」
安妮點了點頭,那位戴維斯少校,仍然一臉不相信的神氣。
木蘭花道:「外面風大,請進來吧,少校,旅途愉快麼?」
木蘭花這樣說,本來只是一句十分普通的客套語,有遠方來客,這句普通的問候話,是對誰都適宜的,可是戴維斯少校對這句普通的問候話的特殊反應,卻連穆秀珍也感覺到了。
這位少校先是陡地一震,接著,便回頭向鐵門外看了一眼,事實上,鐵門外的公路上,靜得除了風在馳動之外,什麼也沒有。
而少校的神色,在那一剎間,也顯得十分驚惶,一個久歷戎馬、經過嚴格軍事訓練的人,是不應該有這種張皇的神態的,而他居然現出了那樣的神態來,那就證明,他的心中的確是有什麼事,令他真正感到害怕!
而且,他也不和木蘭花客氣,在回頭望了一眼之後,就搶先急急向屋子走去,木蘭花、穆秀珍和安妮三個人,跟在他的後面,在他們相繼走進屋子之際,木蘭花回頭向安妮施了一個眼色。
安妮立時點了點頭,她走在最後,在關上門之後,木蘭花、穆秀珍和少校在客廳裡。
而安妮雖然極想留在客廳裡,聽少校談他來訪的目的,和那座奇怪的寺院中,會無風自動的那口大鐘的奇事,可是她卻並沒有在客廳中多停留,而逕自上了樓梯,來到了二樓的工作室中。
安妮一進了工作室,就在一張控制台前坐了下來,用熟練的手法按下了一個鈕掣,在她面前的一組九幅螢光幕,就一起亮了起來,幾秒鐘之內,安妮就可以在那九幅螢光幕上,看到木蘭花住屋四周圍的情形了。
從戴維斯少校剛才如此受震動的情形來看,他的旅途之中,可能有什麼意外,也可能是他的安全正受著威脅,安妮完全明白木蘭花的意思,所以安妮才會在工作室中,察看屋子四周圍的情形,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可疑的人物跟蹤而來。
但是,從螢光幕上的情形來看,卻又平靜無事,公路上要隔好久,才有一輛跑車疾駛而過,那些疾駛而過的車子,絕沒有任何想停下來的跡象。
屋子左右和後面的空地上,也一點沒有異動。
不過,安妮是一個對一切的事情都十分負責的人,就算她在做的事是枯燥乏味的,她還是一樣全神貫注地做下去,不會中斷的。
沒有可疑之處,她應該給木蘭花一個信號,她按下了控制台旁的一個掣,連按了三下。
這時,在客廳中的木蘭花,正在一個小巧的酒吧前,為客人斟酒,而她的視線,則注視著牆上的鏡子。在鏡子中,她看到鋼琴上,有一盞小小的綠燈接連閃動了三下,她知道,那是安妮在告訴她,完全沒有意外。
木蘭花轉過身,走出酒吧來,將酒遞給坐在壁爐前的戴維斯少校。
戴維斯少校的神色很不平靜,他的樣子很神氣,可以看得出當年他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雄姿,但是歲月不能掩飾他臉上的皺紋,更無法掩飾他心中的驚惶。
穆秀珍一直盯著戴維斯少校,想聽他開口,可是少校卻只是一口一口喝著酒,一聲不出,直到他喝完了酒,他才呼了一口氣。
木蘭花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道:「是不是有什麼意外?」
戴維斯少校的神情有點迷惘,他搖著頭,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木蘭花皺了皺眉,雖然她精於推理,往往可以推測到一些人家未曾說出口來的事情,但是,對於戴維斯少校這一連兩聲「不知道」,她卻也無法知道那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