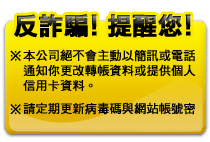愛盟‧保釣-風雲歲月四十年

那些年,他們肩挑家國氣運 童永昌
仔細回想起來,父親從未深談過海外的故事。營區高聳的松樹、筆直的將軍道,以及營房裡揮之不去的、夾雜噴漆與汽油的味道,是我們對他事業的主要記憶。反共愛國聯盟則具現化為每年的聚會。在這些日子,父親會換上便服,帶我們出席充滿歡笑、美食與溫馨的會場,偶爾參加一點抽獎,還有歌唱。
這樣,愛盟在我們的童年記憶中,便與愉悅劃上等號。那是父親難得放鬆的場合,也是他忙碌的軍旅生涯中,少數能闔家同樂的機會。
民國八十九年,我們的國家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朝野上下對新世局表達的各種疑惑、不安或喜悅,與我們在那年年中感受的衝擊相比,多少有些不真實。父親在病床上,看著電視宣布在野黨勝選,輕輕說了一句:「正好可以休息一下了。」誰知卻是永遠的休息。大國家面臨重組之際,我們的這個小小家庭,也正歷經巨變。
整理遺物是一個重建的過程,但也就在這些時候,看著父親過去的文件、照片與檔案,才深覺自己的一無所知。偶然的機會裡,課堂要求學生任選一份雜誌,詳述其始末,正在苦思對象時,想起書房裡數大卷的《人與社會》月刊,父親既列名創刊委員,或許正可藉此機會,探尋他的過去足跡。
報告的成果無足道,但過程卻彌足珍貴。父親有兩篇保釣運動的紀錄,一為刊登在《人與社會》月刊六卷三期的〈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以報告書的形式,條列記載釣運各階段事件;復於民國七十四年撰寫〈沒有英雄的歲月〉,收錄於愛盟的回顧文集《風雲的年代》,以較為感性的筆法,重述當年的愛國運動。這兩份文件以及《人與社會》、《風雲的年代》收錄的文章,即是我當年對釣運與愛盟歷史的全部認識。
愛盟源自保釣,保釣則源自中日兩國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論。「固有疆域」的取得,既是國際法問題,也是歷史問題,中日兩國孰先發現釣魚台、是否持續佔據,既有爭論,亦難有共識。但日本於清廷割讓台灣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將「尖閣群島」判屬「台北州」所有,應無疑義。台北州既歸還中國為台灣省,尖閣群島改為中屬之釣魚台群島,實亦有法律依據。但歷經戰後局勢的改變,美國實際掌控東亞的政治秩序,已有意將釣魚台歸屬最欲拉攏的盟友日本;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因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全賴美國的支持,對於美日的行動,雖有不滿,卻難有實際行動。一九六九年開始,日美既有歸還琉球的共識,而釣魚台則依日本主張,歸屬琉球;自由中國此時卻面臨共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步步進逼,聯合國之席位既賴美國保全,更難以強硬姿態向美日抗議。
父親於一九七○年春天,以上尉軍階赴密蘇里大學就讀,面對的就是此山雨欲來的局勢。政府既困於時局,毫無作為,留學生難免心急如焚,深恐誤國,各地紛紛成立保釣組織,期能發揮影響力。在當年末,父親趁寒假由密蘇里出發,先西再東,旅遊各州,順便聯繫同志。在得知全美各地將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舉辦遊行後,即聯繫密州各地,成立行動委員會,遊行順利舉行,也使活動主辦人信心大增。
「一.卅」遊行是保釣運動初試啼聲,國內固然引發回響,亦促使海外學人進一步構思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這種樂觀氣氛,並非沒有隱憂。回顧當年參與者的紀錄,都指出保釣成員左、右、獨派紛雜,雖然短暫統一在捍衛國土的主張下,實則暗潮洶湧,伺機而動,其中自以左派學生著力最深。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顧忌國際局勢,不得不「持重」;留學生抗議、遊行等行動,在當時國內保守風氣看來,又不免有動盪、激進之慮,甚且指學生將「為匪所利用」,海外工作單位亦反應遲緩,政府「懼亂」而不能「用亂」,其結果是錯失民氣,喪失了保釣運動的主導權。這種現象頗令學生憂心忡忡。父親在一封給大使館武官的信件中,也明白告知此問題:
本運動因主題意識及口號之響亮,引致留學生廣大之反響,由於事前並未及時疏導,事起後徒以壓制、不合作、不參與之方法進行,反而引致反感,芝加哥區之受攻擊最烈,此為最大原因。……但如吾人以全盤作用觀之,亦足可因勢利導此一團結力量,走向有利方向,如僅處處防範,適足以授人以柄,而行動反處處受制,被動必敗,非兵事而已。
信中尚有建議數條,周書楷大使函覆,僅稱「交本館有關單位參研」,考量到當時國內的基調是務必持重,使館人員自然消極以對。
這封信反映了當時愛國學生面臨的困境。他們既主張國府享有中國正統,但又無法為政府的軟弱作為辯護,不免使自己在對抗左派學生統戰時屈居劣勢,更有甚者,國內時時透過關係加以勸阻,前有強梁,後有誤解,真可謂腹背受敵。部分人士遂趨於淡漠,而釣運組織遂漸由左派學生掌握。釣運分裂並變質,已是時間問題。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的「四.十」遊行,是美國保釣運動的最高峰,也是最後的一次大團結行動。遊行由紐約保釣會主導,全美各地留學生蜂擁而至,父親大約在此時也參與了相關會議,而據觀察,左派學生既著力攻擊政府,總結的會議也有一盤散沙、茫然莫從之感。但左右兩派學生的矛盾,已越見明朗,釣運的主軸即將轉變,使留學生界走向全然不同的方向。
今天回頭評論政府的作為,「錯失先機」大概無疑義。理性而言,釣魚台之喪失,即將成為國際現實;我國在聯國的席位,亦朝不保夕,值此不可為之局面,政府之持重,自有考量;反之,左派學生之全面倒戈,亦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群眾運動本是情緒行為,既不能泯於未行,又不能導於已發,舉措失當,徒使留學生與政府反目,彼此誤解,虛耗力氣,既然席位終不可爭,何妨與留學生同聲氣?但若從大環境而言,這卻又在情理之中。政府在長期的保守環境下,固然善於理性為政,但卻不能掌握百姓的觀感與心態,在國內尚可依靠治安法律、新聞管制製造和諧,在國外就難以平復留學生情緒。倘不能從中習得教訓,海外聲望恐將一敗塗地。
「四.十」遊行雖是重大活動,但參與者到底佔海外學界多大比例,仍有疑問。雖有留學生熱中國是,但亦不乏潔身自愛者,而釣運由民族主義情懷,一轉而為政治上的「排我納匪」後,大部份非左派的留學生心灰意冷,大約都影響了此時同學參與活動的意願。四.十遊行結束後,除短暫因車禍療養外,父親繼續在密大辦理各種活動,諸如中國之夜、中華文物的展示、國片播放等,這些行動既在推動國民外交,亦在標榜中華正統。結束密大學業後,則一方面繼續聯繫各地學生,一方面持續參加愛國運動。一份他拜託同學幫忙的信函,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氛圍:
謹寄上「致美友人書」信稿一份,請以最快方式送交當地報館,最好約幾位同學一起去,欲求時效,不得已也,拜託:請於刊出後,寄下下報紙一份(刊出刊就行),擬彙集後送交尼克森及國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伙伴向來愛國不後人,舉手之勞,量必能共襄此舉,也不致令我有白開幾天夜車之感,謝謝。……黃石行,人太少了點,伙伴,伙伴,能來就來,長考頻頻,會走火入魔的。
「致美友人書」內容為何,今已不可考。想是希望動用輿論,聊盡人事。黃石行則是當年稍晚在黃石公園舉辦的大會。此信的對象是台灣同學,從中也不難推斷,同學對這些政治行動興趣缺缺。這或許也反映了一部分留學生的看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至五日在密西根安娜堡召開的國是大會,在今天被視作左右兩派決裂的分水嶺,從各種材料來看,政府實已掌握了相關動向,並且不願重蹈該年的覆轍,積極投入指導,提供對策。父親寄給芝加哥副領事的信件,提及需要「知己知彼」,可見此時愛國學生已有較多的資源,並且有聯繫、組織,以備九月的大戰。然而即便部分愛國學生參與其中,仍無法阻止國是大會最終左傾,甚至提出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等決議。隨著中共在十月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釣運的左右之爭看似大勢底定,左派的學生獲得了最終勝利。
當我打出「最終勝利」這四個字時,不免是感到有些趣味的。在我們成長的一九九○年代,自由中國地區正以高所得、高文明的形象,遙遙領先共產中國。另一方面,當年參與保釣運動的愛國學生,大部分學成歸國,成就卓著。也因此,直到自己進入大學,開始閱讀歷史,才「驚覺」釣運當年,竟是由左派學生取得優勢,而愛國學生其實頗有喪家之感。
這個誤解,顯然是因沒有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當下,當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全球皆認為中華民國即將消滅之際,左派的學生早已抱定中共的大腿,積極學習馬列毛主義,準備投身「新中國」;另一些對中共素無好感的學生,也只能徒發悲觀主義的論調,一邊「唱衰」中華民國,一邊打算定居海外。所謂的愛國學生,其所抱持的國家主義情懷,並非趾高氣昂的勝利者之姿,而是四面楚歌的孤臣孽子之態。父親在十月廿五日當晚的紀錄,是很好的寫照:
十月廿五日我國被「迫離」聯合國,當晚我走在加拿大首府渥太華冰霜滿地、淒冷的河邊,遙看加國電視以“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報導國內木然肅立唱國歌的小學生,並以憐憫的口吻「悼念」台灣即將就此消失,那時內心的隱痛、機動無以復加。我發誓此生絕不讓邪惡得逞,中華民國的歷史永不會留白。
在左派學生歡天喜地,與中共代表團共慶勝利的同時,愛國學生反而因激憤,找到了新的動力,經過十二月廿五日的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會議,匯集成反共愛國聯盟,其效率之高,意志之堅,氣勢之盛,恐非安娜堡國是會議可以匹敵,亦非釣運一開始的參與者所能預料。
平心而論,在「保衛中華民國」與「保衛釣魚台」兩個議題,前者自比後者易獲得留學生回響。留學生在國內已受多年的反共教育,雖然到海外改變態度者不少,但中共政權的負面形象,仍是多數學生熟悉的課題。「仇日」固然有之,「仇共」豈在少數。此外,留學生既來自台灣,亦不願家鄉同胞受中共摧殘,左派的態度越驕傲,越否定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越會激起反感。從政府的著力而言,保土運動既有民族主義色彩,在中共獨霸民族主義大纛後,我國很難加以辨析,但若將議題鎖定反共,則可跳脫民族主義困境,運作起來自也較為有利。
然而這種客觀分析,不能完全說明愛盟的出現。留學生的憤慨仍是因深切體認到國家的危急存亡。左派學生在當年是否受到中共的實際操控,不得而知,但至少就當事人的角度而言,他們也自認是一片赤誠,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難免令人覺得是落井下石,更何況,大部分學生還是受台灣政府栽培才能留學海外;相形之下,愛國學生雖然後來在國內成就非凡,但在七○年代當下,他們多半沒有顯赫出身,在美國本可安家立業,卻願意在國家危難之際,雪中送炭。與左派學生勝利者的姿態不同,愛國學生「退一步即無死所」的領悟,或許更是關鍵。許多早期置身事外的學生,因此契機,投身愛國運動,在今天保留的紀錄中,他們不乏受學業、事業所困,自顧不暇者,但人人奮不顧身,以國家為己任;出錢出力,唯恐後人。
中共在進入聯合國、與日建交後,即因外交考量,不再積極爭取釣魚台,多少打了左派學生一耳光;鐵幕傳出的文革訊息,也扭轉了海外對共產中國的認識,多位當年熱烈支持中共的海外學者,不少人如今也羞於回顧,僅能顧影自憐地回味年少輕狂。與之相比,本被國際認為即將滅亡的中華民國,卻在七○年代一片團結自強的氛圍中,屹立不搖,歷史的嘲弄在此,至少在這個案例中,歷史也還了公道。
父親在一九七二年春天,亦即愛盟成立的隔年返國,但仍持續關注愛國運動。除參與《人與社會》月刊刊務,也與盟員保持聯繫。一九七八年美中關係動搖,卡特總統似有與中共建交企圖。國內逢此山雨欲來之態,提供愛國運動發揮空間。一九七八年八月,回國留學生召開自立自強大會,《人與社會》月刊也於當月刊出《保釣運動》專號,期使再興當年的反共愛國氣象。愛盟成員再度聚首,成立回國盟員聯誼會。十二月十日,反共愛國大會在僑光堂舉行,卡特宣布斷交後,愛盟也隨即參加中視錄影,發布聲明,並主持中南部的愛國大會。當美國代表團抵台時,愛盟也負責居間協調,疏導抗議學生,以掌控場面、穩定人心。在後來的自強年元旦升旗、各種愛國教育場合,都有愛盟的身影。一如一九七一年,當國家動盪之際,愛盟再度投身護國運動。
這段期間的愛國運動有兩個重點,簡言之為外抗中共,內抗黨外。抗擊中共自不待言;黨外人士主張衝撞體制,也不能容許。愛盟的核心理念,既是保衛中華民國,在黨國一體的環境中,難免倒向國民黨。在此背景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呼籲體制內改革等右派、保守作為,也在情理之中。
對黨外的批判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七○年代釣運中仍聊備一格的台獨勢力,隨八○年代黨外運動的勃興,已挑戰愛國運動的本質。呼籲改革,容或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但主張獨立,不啻危及中華民國的存在,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比中共威脅更大。既然台獨與中共都危及中華民國的生存,指責黨外人士為「中共同路人」,也是當時的特點。在一黨獨大的時代,國家又因危難意識,上下一心,反共愛國既是主調,縱使有歧見,也難有發揮空間。愛盟的理念儼然成為社會主流,所向披靡。
但九○年代一系列的巨變,對愛盟卻彷彿不太友善。
蔣經國總統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一開始,李政府似乎仍意圖沿襲早期的國家方向,並曾接見愛盟成員,但一連串的政治變革,似乎已經暗示,愛盟所熟悉的八○年代,將會一去不返。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例,從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與其說是終結兩岸的敵對狀態,毋寧說是宣告我國放棄與中共爭奪中國的正統。連帶後來的本土化教育、新台灣人認同,再到兩國論,我們似乎可以判定,廢除戡亂條例本與和平無關,「關係正常化」實在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鋪路。政府既無意續爭正統,在九○年代初成立政團的愛盟,竟反而成為媒體口中的「特殊立場團體」,甚至令主流政黨領袖避之唯恐不及。黨外團體則在解除黨禁後,組織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逐步挑戰國民黨政權,在攻城掠地之餘,也推廣理念,台獨登堂入室,成為可以大方討論的主張,這難免讓當年奮勇鏖戰的愛盟成員,有昨是今非之感。
外在大環境變動,挑戰著愛盟的信念;第三黨運動導致的分裂,也讓許多成員困擾。不滿於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以及國民黨的腐化,成立於一九九三年的新黨以新銳之姿挑戰國民黨的霸權,部分愛盟成員加入其中,引起分裂。這段不愉快的過往,早隨時間推移、時局改變而消失,政治是一時,友誼可永久,且從今天來看,愛盟成員就令有不同黨籍,其核心理念,仍可謂為同志。
無論如何,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從某個角度看來,或許是宣告「美好的時代已過去」,隨著民進黨在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國民黨即使取得省長與首次總統直選的勝利,卻似乎已日暮西山。另一方面,兩岸的互動頻繁,交流日盛,面對這個敵我逐漸模糊的「和解時代」,既反共,又反獨的愛盟似乎也有點茫然。任孝琦女士在《有愛無悔》一書〈和解時代的迷惘〉一章的最後,引述了劉志同先生的一段話:「危機或許也是轉機,現在是愛盟人思考未來要走哪個方向的時候了。」
《有愛無悔》出版於一九九七年,是愛盟二十五年活動的一個總回顧,但當年所謂的「危機」,包括國民黨的本土化、新黨運動、總統直選、兩岸飛彈危機等等,和二○○○年相比,似乎都顯得小巫見大巫。
公元二○○○年,民進黨以未過半的選票,在三組候選人中領先,贏得選舉。此舉引發國民黨內討伐李登輝的聲浪,指控李扶植台獨勢力,分裂國民黨,使國民黨丟掉政權。李最終在壓力下辭去主席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就像各新興國家的「萬年執政黨」一樣,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國民黨雖非一無可取,但也難逃腐敗、顢頇的命運。在野黨在歷次選舉中站穩清廉、改革等正面評價,最終取得政權。事後來看,二○○○年的政黨輪替幾乎無可避免,因為執政黨的候選人得票最少,即使在另兩組候選人中發生「棄保」,執政黨仍難以延續政權。
但與各新興國家不同的是,除了政府效能以外,政黨尚有國家認同的重大差異。五十年的一黨獨大,多少有點國隨黨生的印象,而國民黨在九○年代的本土化,則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認同,隨著國民黨交出政權,中國認同也看似搖搖欲墜。
新政府著力剜除國民黨時代的符號,代之以新的意識形態。中國認同成為禁忌,民國歷史也成為「他者」,國家以一種陌生的方式,重新塑造認同,對於任何參與早年愛國運動的人士而言,大概都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這種集體的焦慮,在二○○四年的大選攀至高峰。緊繃的選情被一顆子彈攪動,執政黨哀慟不已,在野黨卻認為是自導自演,最終政府連任,在野黨則佔據總統府前的廣場,展開長期的違法抗議。
遊行抗議,本來是釣運的常態;但違法抗爭,對於早年呼籲穩健理性的愛國人士而言,大概是全新體驗,而呼籲以大局為重的政府高層,在當年卻提倡衝撞體制。我猶記得在某次愛盟聚會結束後,成員信步到廣場的經驗,那也是首次,七年級的我們接觸到抗爭的實況;而電視上出現的,愛盟長輩在宣傳車上發表言論的畫面,也令人深為動容。政黨輪替造成的主客易位,也連帶翻轉了習以為常的政治文化。二○○六年的紅衫軍運動,更出現在野黨擾亂國慶等舉止,過去看似荒唐的行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卻找到了合理性。
世局的變動,很容易讓人迷惘。當年左派的學生回顧歷史,不免悵然,而愛國學生或許亦作如是觀。反共的「共」變了,愛國的「國」也變了。早年捍衛中華民國的鬥士被打為「共黨同路人」,而反政府成員搖身一變成為建國烈士。愛台灣本與愛中國不牴觸,如今後者成了禁忌;而當年的大敵中共,卻陰錯陽差,「看似」成了中華民國的好友。
但觀念會變,論述會變,「實踐」卻不會。
在一次愛盟的聚會中,趙林先生曾指出,愛盟的政治主張,未必實現,「釣魚台到今天還在日本人手裡」,但愛盟人對國家建設付出的心血,卻有目共睹,這是確論。呼喊「愛國」並不困難,假愛國之名行惡,更大有人在;真正的愛國除了言說,還有實踐。部份左派人士在數十年後,雖然也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錯誤,但在抱怨自己多年被列入黑名單之餘,對於愛盟成員在國內的發展,未嘗沒有一絲怨懟;而黨外人士則指愛盟為國民黨打手,反民主的幫兇。
平心而論,國民黨政府對反政府人士的策略,自有失當之處,但當年左派學生選擇親共,卻非國府強迫所致;反之,愛國學生在危急存亡之秋,願意返國協助建設,又豈能逆料後來的發展?至於指責愛盟專為國民黨打手,既高估了愛盟與國民黨主流的關係,也罔顧了一項基本事實:愛盟成員投入國家建設數十年,與黨外人士相比,其貢獻孰重孰輕?在國家發展的路程上,民主建設自有其比重,但除了反政府,恐怕尚有許多重要工作,需人努力,而愛盟在此過程中,大約亦問心無愧,因為他們始終站穩守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即使在和解時代,與民進黨、共產黨不再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但原則既把持住,愛國的根本理念也未動搖。
但這些關於變動與理念的看法,我已礙難從父親口中得知。二○○○年新政府宣示就職八天後,他溘然長逝。即使在人生的最後十多年,也因職務關係,很少參與政治活動,對此,愛盟也深為體諒。他未及給予我們任何思想上的引領,但今天保留下來的這些文件,以及愛盟各位長輩的經驗傳遞,卻成了我們這一代,思索國家未來方向時,極好的參考座標。
愛盟成立至今,已四十年,長輩們當年面臨的世局,與八○年代出生、成長於九○年代的我們相比,有異有同。相同之處,是中華民國地位岌岌可危;相異之處,除了兩次的政黨輪替,還有兩岸關係的大幅進展,除此之外,最令愛盟陌生的,或許是中國認同的退潮。在歷次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遠不能與自認「台灣人」者相比,甚至「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也在極度萎縮。
雖然有些人會將中國認同的退潮,歸因於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二十年的本土化運動,但平心而論,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徹底接納資本主義,走上新加坡式開明極權的路線,已有大國崛起之勢。其以中國正統自居,比四十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政府欲與其爭正統,可著力處卻不如四十年前更多。復因中共於國際上處處打壓我國地位,民眾固然因情緒憤慨,不願被劃歸「中國」;政府領袖亦須於中共限制之中,圖一解套辦法。李登輝時代的兩國論是其一,陳水扁時代的獨立是其一,馬英九政府的一中各表也是其一。中共獨占「中國性」越強,中華民國的「台灣性」也會越強,這在客觀上壯大了台獨思想。
主觀情感上,兩岸分隔六十年,在本省人而言,本與大陸感情不深;即便外省第二、三代,對大陸亦缺乏情感認同,七○年代的愛國人士,大有可能出生於大陸,但其子嗣未必保存對「故土」的信念。弔詭的是,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反而可能因接觸而深覺雙方差異過深。「因陌生而認同,因認識而分開」,兩岸關係,未嘗不如此。另一方面,國民黨早年治台的政策、與黨外運動的衝突,也是當前仇中意識的重要原因。七○年代,猶可以「台獨沒有道理」一以蔽之;二○一一年的當下,要說服民眾,恐怕沒有如此簡單。
一九九○到二○○八二十年間,政府意圖建立新的國家認同,卻反而製造了更強烈的分化與隔閡,直到如今,國家認同還是社會的唯一議題,所有其他關於經濟、環保、教育的重大政策,在認同問題前,都顯得不甚重要,乏人問津。候選人沒有政策辯論,只有國族對抗,而民眾也懶得深入思考政策,關心政治僅僅意味關心認同,而關心認同,又往往爭執於是否插國旗,是否使用「Chinese Taipei」而非「China」,以致於重回國際社會、取得免簽,反被稱為「出賣」;因經濟政策失當造成競爭力銳減,卻無人究責。對照當年某些人批評國民黨政府不應退出聯合國,實在令人驚嘆。
認同是否重要,見仁見智,基於各種情仇,我們大概礙難尋求一致的認同,但這實無妨我們持續貢獻心力於台灣社會。台灣人、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這些身分的認同若無高下,那麼何須主張只有某種認同才可以參與國家建設?至於基於認同引致的,對國家未來的不同看法,或統或獨,則仰賴理性的辯論與協商,又豈能說凡主張某一認同,便只能接受某種主張?中華民國是當前的最大公約數,此雖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政治現實。既然我們不能肯定,台獨必然會帶來完整的國際法人格;而一九四九年前後聯繫的感情、記憶與歷史,又不可能完全切割,實不需揚棄中華民國,另換國號。另一方面,中共既不願放棄統一台灣,我國又不可能如某些人士主張,不涉世事、只顧自己,則維持中國國號,亦可在兩岸互動中,爭取有利籌碼,這顯然都比貿然獨立,更有利於國計民生。當年輕人徘徊於中國與台灣的零和認同時,愛盟四十年的歷史,正好驗證中華民國路線可長可久之道。
兩岸的發展是統是獨,或者是否有統獨之外第三條路的可能,尚未可知,並且仍繫於中共的態度,非台灣一廂情願可以解決。但隨著經濟起飛、民智開化,中國大陸也正經歷急速變動。共產黨的統治表面上與時俱進,但民眾對一黨獨大體制的懷疑、不滿,也與日俱增。就在這篇文章完稿之際,溫州發生了重大的動車追撞意外,官方的顢頇無情,與網路世界的憤怒形成強烈對比。兩岸「八零後」的交流,也在逐步拓展,武力上「反攻大陸」固然難以實現,但思想與生活的潛移默化,卻正在發生。某年在台招待大陸學生,在經歷一週的遊訪後,這名有意報考大陸公職的青年說:「這裡太好了,還是就這樣吧,別被大陸拿走了。」這簡單的一句話,或許也為兩岸的未來,寫下無限可能。
歷史的當下,總令人深感震撼;但遺忘的速度,也往往讓人吃驚。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也是愛盟成立的四十周年紀念,長輩們既有重出文集、留下紀錄的打算,身為一個八十年以後出生的晚輩,未曾親見當年的風雨,本來沒有資格撰寫任何文字的。但既曾言及願意貢獻心力,也難違陳義揚校長的抬舉,遂提筆(實則是「按鍵」)寫下這數千字心得。這篇文章,因為個人材料的限制,是以父親為中心。父親當年曾在〈沒有英雄的歲月〉中,提及愛國運動沒有英雄,而是全體的投入奉獻;但反過來說,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其實人人都是英雄,我亦以得識英雄,與有榮焉。
謹以此文向愛盟的長輩致敬,敬他們的無私奉獻;也敬他們那些年,肩挑家國命脈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