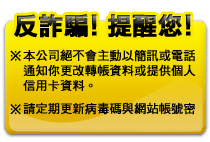聞嗅慣了的葉子煙的煙霧在燈下嬝繞著,閨女盈盈靠在櫃檯一角,一動不動的坐著,不時的眨著眼。
黿神廟前的夜晚,本就夠熱鬧的了,到了黿神節的前夕,更熱鬧得勝過城裡的鬧市,從土坡下面開始,一路布篷挨肩搭背的張起來,每個棚前都點燃著馬燈和彩燈,把夏夜溫寂的大氣燒得一片火紅。星空很繁密,來拜廟的人群更繁密,天上的流星還在星群中間飛跑著,不遇什麼遮攔,人呢?只有挨挨擦擦的擠,誰也休想跑上一步。
也許難得逗上這樣晴和的天色罷?
那說傻不傻,說機靈又不機靈的小夥子怎麼還沒見著影兒呢?……儘管爹那暴暴的嗓子還在耳邊飄響著:「我不准你跟那些扛鹽伕和莽船人閒搭訕,不准你去招惹他們,這些沒根的浪漢,十個有十個不是好人!」好像他多年來就沒改過他那種神經兮兮的固執,至少,那小夥子一眼看上去,就跟那些浪漢們不一樣,他是不會相信的,當初他也曾多次這樣吼罵過媽,使那許多原本平靜的夜晚,平添了許多咆哮、咒咀和眼淚……爹說媽走了,人人都跟著傳說媽走了,爹在酒肆裡昏天黑地的酗酒,講了媽許多莫須有的醜話,說她怎樣跟三花臉,怎樣跟長鬍子的浪漢,人們居然就相信他,並且跟著傳說這,傳說那,繪聲繪色的,把沒有人眼看的事情都說成真的。
真相如何?自己也不知道。
只還隱約記得那些在爹咆哮聲裡戰慄的夜晚,爹臉色鐵青,兩眼噴火,額頭的青筋暴凸著,拼命揪著媽披散的頭髮朝牆上撞,一面說些昏亂得不能連貫的話:你甭想拿什麼感恩依順的甜嘴來哄騙我,你不是木頭刻的,你說,你是不是偷了三花臉?我是殘廢人,沒老婆也過得了日子,你認了,我放你走!我不戴這頂綠帽子……天知道哪來的三花臉?要等他脾氣發過了,媽才跪著說好話,說絕沒有這種事情,全是你憑空想出來折磨人的,假如在城裡不好,就搬下鄉好了。
下了鄉,三花臉沒有了,換成個長鬍子的船戶,還是三朝兩日的一頓罵,一頓打,二天媽眼上貼膏藥,頭蒙在被裡,委屈不盡的哭……。
「盈盈,媽的乖女兒,媽也許有一天,就這樣含冤不白的死在你爹手上,你爹是個好人,卻是個瘋子!……他怎樣古怪的想,就以為他想的就是真的,媽若真像他想的那樣人,當初就不會找著他嫁了。」
媽究竟去了哪兒?自己根本不知道,問爹,爹冷著臉子說:「別問她!那不要臉的,跟那生長鬍子的野漢子跑掉了!」
「老陶的老婆,跟那長鬍子船戶跑掉了!」幾乎立刻就聽到了這種風播的迴聲。
星空很繁密,又有一顆曳著長長光尾的流星在飛跑著,突然滑落到高高的黑裡,再覺不著蹤跡了!那邊亮著的船桅燈也很繁密,它們夜夜亮著,它們是一些地上的星子,但也會在朝來的霧裡滑落,跟著滑落的是一些人臉。
在這被燈火燒紅的夜裡,不知怎的竟是想著那個看來傻氣的小夥子,偏又想起那些使人心潮的往事,跟著這些升起的,是爹陰鬱的眼和緊鎖的眉,也就是那眼和眉的濃密的陰影,把自己鎖禁著,禁在身後這座遍地生苔的院落裡,每一塊石上的苔痕,都是一張陰鬱的人臉,每一張那樣的臉上,都有著爹的影子。
天知道媽走後這五年的長日子是怎麼過的?記憶愈朝深處推,瀰漫著的黑霧越是濃,混混沌沌,更加尋不出什麼蛛絲馬腳來,能替媽捲逃這樁事下注腳,只是失去她之後,家便寂寞冷清下來,連風也留不住,而爹只有一把琴和一罈酒,醉意醺醺的拉走了一個黃昏又一個黃昏,雲也僵凝,風也冷,那琴弦總像在吐著什麼,說著什麼?日復一日的,幾乎拉的是同樣的調門兒,慘霧在弦下湧聚,愁雲在弦上匯結,叫人不忍卒聽。——似乎比媽在家時夜夜聽爹的咆哮更慘了。
只有守在香棚裡的時辰,才覺得離外在的世界近一些,但總像隔著一層什麼,隔著什麼呢?自己曾在園子裡捉過一隻螻蛄蟲兒,把牠裝在一隻小口的玻璃瓶子裡,放在石階上看著牠,螻蛄蟲靈活的頭顱轉動著,牠一定看見瓶外的天地。花和草,土和石,牠便用力的爬著,爬著,但總跌回原來的地方,自己也就是那隻螻蛄蟲兒罷?但比那螻蛄蟲兒聰慧些,至少還能知道有那麼一層阻擋,不願費力去掙扎,只是坐著,沉在一剎而來一剎而去的迷惘裡,用那些迷惘編成一個結又一個結,只能編,卻不能解開……
那看來傻氣的小夥子怎麼還不來呢?
「三個銅子兒一小把,五個銅子兒一大把,隨意挑罷!」有買香燭的人進香棚來了,她便照例的這樣說著,站起身來,替他們斟上一盞熱燙的麥仁茶,再照例的收一圈兒空茶盞,把久坐的客人朝廟裡趕。
點燃著方燈賣吃食的小擔兒連著挑過去,篤篤的敲著毛竹片兒,賣西瓜枒兒和成串水蘿蔔小販,怪腔怪調的發出一些高過人聲的呼喊。人頭黑鴉鴉的順著鑼鼓點子滾動,這麼多的人,該把崗坡壓塌了。
一隻蛾蟲不知從哪兒飛進來,受了驚似的抖著粉翅,叮叮的撞著燈罩兒,又飛繞一個圈,把思緒引至另一個打得很緊的死結兒上。……媽走前那一天,爹又舊話重提,咬牙切齒的說起那個長鬍子的野漢,說他親眼看見那個人,斜揹著個扁扁的小包袱,在香棚門口兜來轉去的繞圈兒,說那人存心來接她的。
「你這賤貨,怎不跟他走?死賴在這兒哄騙我做什麼?潘金蓮謀害武大,你是想謀害我,讓我七孔流血死給你看?」
……「天喲!」媽雖捱了掌摑,仍然朝爹跪了下來,抱著他的腿,發出撕裂人心的哀叫說:「好人,天怎會讓你得了這種疑心病的?我自願跟你苦,跟你熬,這十幾年來,前世差你欠你的,論補也該補夠了,你不能這樣平白的冤我,鬼見著什麼長鬍子的大漢了?」……
「那你跟我到老黿塘上去發誓去!走呀!」爹動手扯著她的腕子,扯得她那對碧玉的手環叮噹擊打著,媽跟自己講過那對手環,她買它們時,正是她在戲臺上最風光的日子。……
「你不用這樣拉扯我,莫說到老黿塘上對著神黿發誓了,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也願去,只要你肯相信,朝後不再活活的折磨我。」……誰知道呢,她竟是第二天夜晚走了的,在她發過誓之後。
她忽覺兩眼有些溼,便用笑來壓,硬把淚水壓回去了,滿天的星子似乎晃了一下,一個人笑著走進了香棚。那正是傻小子狄虎。
「哦,」她笑得更深些,兩頰的酒渦起了旋動,朝他說:「怎麼這樣躡手躡腳的?活脫像個——賊!」
「我來了好一會兒了。」狄虎說:「來買兩把香燭,求那個黿神把我的賊名洗一洗,剛剛我見你在想著什麼,沒好打擾你。」
閨女用霎著的黑眼說了一點兒什麼。狄虎又舐了舐嘴唇。
「那個害汗病的大個兒,沒跟你一道兒來逛廟?」
「他?——他叫你罵怕了。」狄虎說。
「我又不是靠罵人吃飯?不罵人嘴會癢!」閨女說:「他惹我在先,對付這種人,最好的法子就是罵,不罵得他狼狽,得不著清靜。」
「你真的很會罵人。」狄虎把奉承話說出了口,又覺得奉承得不甚妥當,——哪有奉承女孩兒家會罵人的?不過,他又立刻想出話來,補正說:「當然嘍,罵人並不是什麼好事情,用在該用的地方,不會吃人的虧,凡人在世,學著什麼都有用處,不是嗎?——學個羊癲瘋在身上,一樣嚇得著人。」
「嘻,看不出你倒是滿會說話的。」
「他們雖叫我傻小子,」狄虎說:「其實我並不傻,我自己知道。在船上的日子不太久,總覺過不慣,三天五日一個地方,飄來飄去的跟大夥兒合不上趟,在人家眼裡,不傻也傻了。」
「既是過不慣,那你幹嘛要上船做事情?」
「人總要混飽肚皮啊!」
「哪兒都好混日子,不一定在船上。」
「幹這行,利潤多些,」狄虎倚著門框兒說:「我也不想久幹它,總打算發力幹它三幾年,積蓄些錢,回去買塊靠路邊的地,搭起個茅屋來,做點兒將本求利的小買賣什麼的。」
他自覺今晚上說話很順暢,言語也多起來,因為每當自己說話時,對方都那樣的半仰著臉,手托著下巴,出神的,又饒有興致的傾聽著,彷彿四周一切喧鬧的聲音都沒在她的耳裡,其實他說的,並不是心眼兒裡要說的,也只說些零零碎碎不相干的話,正因為她顯露出願意聽下去的樣子,才逼得他找出話來說下去,越是不相干,說起來越沒有什麼顧忌。
自己說話時,也遇上有人進棚來買香燭,閨女盈盈光顧著聽話,連例行的招呼都忘了打,恁由客人抓了香燭,隨意把銅子兒丟在櫃面上,這雖是細微的小事,看在狄虎的眼裡,不由得滿心感動起來。
他就這樣嘮嘮叨叨說下去,平素他這些言語,在船上說了是沒人聽的,在心裡窩久了,抖出來彷彿都有些酸味和霉味,一塊一塊的泛著溼溼的黏,說他願意開一家小小的野舖兒,能讓趕長途的客人歇歇腿,吃餐熱飯,野店門前若是臨著河,就養些鵝和鴨,當然能有一條小小的船更好,但那只是發貨用的船,只用雙槳不用帆,早出晚歸罷了……一邊說著,一邊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把這些不相干的事情吐給她聽?
但那雙睜大的黑眼睛,像兩隻剛生出黑羽來的天真、稚氣又飢餓的鳥雀,吱吱喳喳的叫著,總得要餵給牠們一點兒什麼,自己早先也餵過兩隻乳雀,當牠們試抖小翅,張開白牙牙的小嘴唧噪時,就餵給牠們一些成熟了的紫黑色的桑椹,她的黑眼睛就那樣的吞飲著自己的言語,彷彿仍沒吃飽的樣子。
「坐著吃盞茶罷,」閨女說:「甭光站著。」
狄虎這才過去,坐的仍是前幾天坐過的地方。
「節後就快開船了罷?」閨女端過茶來說,聲音裡透露出一份難以捉摸的情韻,不敢說是她自興的迷惘?還是對自己離去的關心?
用手旋著那隻熱霧騰游的茶盞,狄虎忽然覺得心裡有些泛潮,閨女站在桌邊,離自己這麼貼近,但這彷彿不是真的,只是一個紙剪的影子,誰知在明天,後天,或是哪一個時辰?飽飽的帆篷像張著的翅,只怕連回憶裡的這樣的影廓也會變成一片模糊的白了罷?何苦要到這兒來呢?一想到開船,就覺得杯裡不是茶,卻是一盞由閨女親手斟上來的苦汁了。
什麼時刻唱過那樣的小曲兒:
人人都說是黃蓮苦喲,
我心比那黃蓮還苦呀苦十分……
「你怎的又不說話了?」閨女的聲音飄過來說:「儘愣著想些什麼?」
「哦,我是在算日期呢,」狄虎說:「下一船運的是豆餅,貨還沒來齊,貨齊後再裝船,總還要兩三天的光景……黿神節,這場熱鬧嘛……算是看定了。」
「甭騙我,」閨女的黑瞳仁兒凝定的看著狄虎的眼睛說:「你不是個愛看熱鬧的人。」
「那也沒辦法,」狄虎說:「咱們這號人,飄流打轉過日子,沒有什麼挑呀揀的了,不能說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有時喜歡的反而得不著,不喜歡的反而送到眼前來,只能說碰著六就是六,碰著么就是么了!」
「你倒是看得開。」閨女說。
「不是看得開,」狄虎聳聳肩,攤開兩手說:「我不是剛說過,那都是沒辦法呀!」
「能轉的骰子總比不轉的骰子好!」閨女忽然吐出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來,下面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但卻頓住了,沒再說下去。正碰著又有拜廟的來買香燭,她就搖搖辮子走開了,把含蘊在話裡的意思留給狄虎獨自去默飲。
外面的鑼鼓聲一陣比一陣響,月光又落在老黿塘半邊塘面上了,正因有月光描勒著,更顯出那深塘的神秘深幽。好些留連在香棚裡的漢子,也都紛紛擠出去看熱鬧去了,閨女還是在櫃角的高凳兒上坐著。
一隻不轉的骰子:狄虎想。
假如老徐那番話是真的,她跟著一個瘋了的爹過日子,該是一顆不轉的么點子!但她從沒鎖過眉,嘆過氣,她明朗得像是無風無雲的天,比較起來看,老徐的那番話,又不像是真的了。
他喝著那盞茶,閨女又過來替他添。
狄虎扯扯她的衣袖,低聲的說:
「昨夜晚,我聽船上有個人,老跑叉港的,他說起你家的事情,說你爹精神有些……可是真的?對不起,我不該冒冒失失這樣問的。」
「除了你,誰都知道的。」閨女盈盈夠坦直的,立時就點頭承認了,問說:「你一定聽了很多很多罷?」
「很多很多。」狄虎說。
「你的骰子還在轉,我的卻不動了,——碗底上現的是一個么。」閨女說:「有什麼辦法呢?他能吃能喝,能講能說,他不承認有毛病,誰敢指著說他有毛病呢?瘋病沒藥醫的,香棚的生意好,賺的錢夠他買酒的。」
「他怎麼總不出來?」
「怕看你們這些外路人的臉。」閨女說:「你要是聽人說了,你就該知道為什麼了!」
「我知道。」狄虎說。
「我媽不是那種女人。」閨女又說:「她決不會做出那種事來的,也沒有那樣一個長鬍子的人,真的沒有,他心裡想著有,就有了!」
「我知道,別人也都這麼說的。」
「還有你們不知道的。」閨女說:「他常在三更半夜裡起來,穿好衣裳,點上燈,對著燈生氣,咬牙切齒的,一個人跟那盞燈說話,又叫又罵的。有時候,他會拎著一盞馬燈,繞著老黿塘打轉,喊著罵那長鬍子的野漢子,要跟那個人拚命。」
「我卻沒有見著過。」狄虎緊閉著嘴唇,兩眼炯炯的,在濃眉的陰影下發著光。
「我是說:有時候他會。」閨女說:「你只是沒遇著罷了。通常在下雨天,響暴雷落大雨的夜晚,他聽著雷,看著閃,就會突然發起瘋來,可是過了那一陣子,雨水淋透了他,他自會一歪一拐的回來,脫下濕衣,再睡下去,第二天,好像沒有那回事一樣。」
閨女歪過身子,拖一拖長凳,背窗坐下來,低著頭,用纖巧的手指引動桌面上的茶水,在胡亂的塗抹著什麼,門前的燈光射不透老黿塘底的黝黯,黑黯沉沉的崖影仍然和月亮互相噬食著。
狄虎猛可的驚震起來,一個閃電似的怪異的感覺掠過他的腦際——閨女彷彿正立在峻陡的危崖上,面對著一個可怕的瘋人,雖然那瘋人確是她爹,但這樣下去,他會做出什麼來呢?
這一切都是無意的,他到這兒來,並沒存心要牽動什麼,天知道話頭兒一斜,竟斜到這事上面來,對於這著事情,他是絲毫無能為力的。……從閨女的坦直吐述,再加上傳言的映證,他幾乎可以確信,那古怪的老頭兒老陶,因為腰部受過傷害,使他無法做一個名符其實的男人,但又因著這段孽緣得到一個絕頂俊俏的女人,這使他身體的傷害沉落到心裡,化成精神的殘疾,疾久成瘋,他能那樣的逼害著他的妻,日後也許會同樣的逼害著他親生的女兒,……他抬頭望著她,幾至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爹發瘋的時刻,你不覺得駭怕嗎?」
「不。」閨女低聲說:「我早就看慣了。再說,他很少對我兇過,除非提起『船』,『船上人』或是『帆』、『錨』、『槳』、『纜』之類的東西,只要跟船字有關聯的,都惹他生氣。」
「我弄不懂。」狄虎把手指插在短髮裡搔著,苦笑說:「我弄不懂這是甚麼樣的古怪毛病?」
「他妒忌,」閨女說:「他始終記著那個長鬍子的野漢子,他相信那個『人』是弄船的。他恨他,也就恨上了叉港上的船,恨上了你們這些船上的人,這幾年,他從不到香棚裡來,總把自己關在後屋裡,他一見著我跟船上人說話,就會氣得發病。」
麥仁兒在茶盞上打著旋,緩緩的沉下去了,狄虎的一顆心也跟著朝下沉,朝下沉,一切的慾望,夢和幻想,也都在隨著沉澱。夏夜是喧鬧的,浪頭般的喧嘩一陣陣的沖激過來,但總沖不透繞在身邊的一圈兒死寂。
「這總是怕人的事情……」他喃喃的說。
「你用不著擔心,」閨女用大大的黑眼斜睨著他,笑了笑說:「再過幾天,船一掛上帆,這事就過去了,大不了你們會講起它,變成一個故事,像叉港上流傳著的老黿塘的故事一樣罷了。」
「不,不是這樣!」
「又怎樣?」
狄虎被她這一激,激出話來說:
「你爹這毛病,早晚會激出事來的,假如……呃呃……假如日後你跟了一個弄船的,他會怎樣?這香棚,又不是鐵壁銅牆,禁不住你這樣的人,也擋不得弄船的漢子,可不是?當然,我這只是說假如的話……」
「假如總歸是假如,」閨女說:「這假如,那假如,千百個假如,沒有幾個會成真的,我爹跟我兇說:十個弄船的,有十個不是好人……」
她還在用手指在撥弄書桌面上的水漬,一道閃電在她眼前划過——她的手被另一隻手用力的壓住了,在昏黯的跳動的燈影裡,她吃驚的去看那張臉,那張臉也正在看著她,他兩眼不知所以的瞪著,仍然是那副愣傻的樣子,認真又誠懇,她想抽回手,卻失去力量,想罵一句什麼,又罵不出口。
「你記住,我是那十個之外的。」狄虎說。
閃電掠過去,他突然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