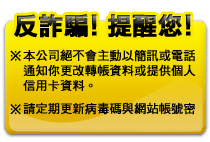朱自清作品精選2:蹤跡【經典新版】

一、《歐遊雜記》序
這本小書是二十一年五月六月的遊蹤。這兩個月走了五國,十二個地方。巴黎待了三禮拜,柏林兩禮拜,別處沒有待過三天以上;不用說都只是走馬看花罷了。其中佛羅倫司,羅馬兩處,因為趕船,慌慌張張,多半坐在美國運通公司的大汽車裏看的。大汽車轉彎抹角,繞得你昏頭昏腦,辨不出方向;雖然晚上可以回旅館細細查看地圖,但已經隔了一層,不像自己慢慢摸索或跟著朋友們走那麼親切有味了。滂卑故城也是匆忙裏讓一個俗透了的引導人領著胡亂走了一下午。巴黎看得比較細,一來日子多,二來朋友多;但是盧佛宮去了三回,還只看了一犄角。在外國遊覽,最運氣有熟朋友樂意陪著你;不然,帶著一張適用的地圖一本適用的指南,不計較時日,也不難找到些古蹟名勝。而這樣費了一番氣力,走過的地方便不會忘記,也不會張冠李戴──若能到一國說一國的話,那自然更好。
自己只能聽英語話,一到大陸上,便不行了。在巴黎的時候,朋友來信開玩笑,說我「目遊巴黎」;其實這兒所記的五國都只算是「目遊」罷了。加上日子短,平時對於歐洲的情形又不熟習,實在不配說話。而居然還寫出這本小書者,起初是回國時船中無事,聊以消磨時光,後來卻只是「一不做,二不休」而已。所說的不外美術風景古蹟,因為只有這些才能「目遊」也。遊覽時離不了指南,記述時還是離不了;書中歷史事蹟以及尺寸道里都從指南鈔出。用的並不是大大有名的裴歹克指南,走馬看花是用不著那麼好的書的。我所依靠的不過克羅凱(Crockett)夫婦合著的《袖珍歐洲指南》,瓦德洛克書鋪(Ward, Lock & Co.)的《巴黎指南》,德萊司登的官印指南三種。此外在記述時也用了雷那西的美術史(Reinach : Apollo)和何姆司的《藝術軌範》(C.J.Holmes:A Grammar of the Arts)做參考。但自己對於歐洲美術風景古蹟既然外行,無論怎樣謹慎,陋見謬見,怕是難免的。
本書絕無勝義,卻也不算指南的譯本;用意是在寫些遊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小小的禮物吧。書中各篇以記述景物為主,極少說到自己的地方。這是有意避免的:一則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論;二則這個時代,「身邊鎖事」說來到底無謂。但這麼著又怕乾枯板滯──只好由它去吧。記述時可也費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覺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難。顯示景物間的關係,短不了這三樣的句法;可是老用這一套,誰耐煩!再說這三種句子都顯示靜態,也夠沉悶的。於是想方法省略那三個討厭的字,例如「樓上正中一間大會議廳」,可以說「樓上正中是──」,「樓上有──」,「──在樓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給讀者整個的印象,或者說更具體的印象。再有,不從景物自身而從遊人說,例如「天盡頭處偶爾看見一架半架風車」。若能將靜的變為動的,那當然更樂意,例如「他的左胳膊底下鑽出一個孩子」(畫中人物)。不過這些也無非雕蟲小技罷了。書中用華里英尺,當時為的英里合華里容易,英尺合華尺麻煩些;而英里合華里數目大,便更見其遠,英尺合華尺數目小,怕不見其高,也是一個原因。這種不一致,也許沒有多少道理,但也由它去吧。
書中取材,概未注明出處;因為不是高文典冊,無需乎小題大做耳。
出國之初給葉聖陶兄的兩封信,記述哈爾濱與西伯利亞的情形的,也附在這裏。
讓我謝謝國立清華大學,不靠她,我不能上歐洲去。謝謝李健吾,吳達元,汪梧封,秦善鋆四位先生;沒有他們指引,巴黎定看不好,而本書最占篇幅的巴黎遊記也定寫不出。謝謝葉聖陶兄,他老是鼓勵我寫下去,現在又辛苦地給校大樣。謝謝開明書店,他們願意給我印這本插了許多圖的小書。
二、《倫敦雜記》序
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承國立清華大學給予休假的機會,得在歐洲住了十一個月,其中在英國住了七個月。回國後寫過一本《歐遊雜記》,專記大陸上的遊蹤。在英國的見聞,原打算另寫一本,比歐遊雜記要多些。但只寫成九篇就打住了。現在開明書店惠允印行;因為這九篇都只寫倫敦生活,便題為《倫敦雜記》。
當時自己覺得在英國住得久些,尤其是倫敦這地方,該可以寫得詳盡些。動手寫的時候,雖然也參考裴歹克的《倫敦指南》,但大部分還是憑自己的經驗和記憶。可是動手寫的時候已經在回國兩三年之後,記憶已經不夠新鮮的,興趣也已經不夠活潑的。——自己卻總還認真的寫下去。有一天,看見《華北日報》上有記載倫敦拉衣恩司公司的文字,著者的署名已經忘記。自己在「吃的」那一篇裏也寫了拉衣恩司食堂;但看了人家源源本本的敘述,慚愧自己知道的真太少。從此便有擱筆之意,寫得就慢了。抗戰後才真擱了筆。
不過在英國的七個月畢竟是我那旅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兒。承柳無忌先生介紹,我能以住到歇卜士太太家去。這位老太太如《房東太太》那篇所記,不但是我們的房東,而且成了我們的忘年朋友。她的風趣增加我們在異國旅居的意味。《耶誕節》那篇所記的耶誕節,就是在她家過的。那加爾東尼市場,也是她說給我的。她現在不知怎樣了,但願還活著!倫敦的文人宅,我是和李健吾先生同去的。他那時從巴黎到倫敦玩兒。有了他對於那些文人的深切的嚮往,才引起我訪古的雅興。這個也應該感謝。
在英國的期間,趕上莎士比亞故鄉新戲院落成。我和劉崇鋐先生,陳麟瑞先生,柳無忌先生夫婦,同趕到「愛文河上的斯特拉福特」去「躬逢其盛」。我們連看了三天戲。那幾天看的,走的,吃的,住的,樣樣都有意思。莎翁的遺跡觸目皆是,使人思古的幽情油然而生。而那安靜的城市,安靜的河水,親切的旅館主人,親切的旅館客人,也都使人樂於住下去。至於那新戲院,立體的作風,簡樸而精雅,不用說是值得盤桓的。我還趕上《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作者加樂爾的紀念──記得當時某刊物上登著那還活著的真的阿麗思十三歲時的小影。而《泰晤士報》舉行紀念,登載《倫敦的五十年》的文字,也在這時候,其中一篇寫五十年來的男女社交,最惹起人今昔之感。這些我本打算都寫在我的雜記裏。我的擬目比寫出的要多一半。其中有關於倫敦的戲的,我特別要記吉爾伯特和瑟利文的輕快而活潑的小歌劇。還有一篇要記高斯華綏的讀詩會。──那回讀詩會是動物救濟會主辦的。當場有一個工人背出高斯華綏《法網》那齣戲裏的話責問他,說他有錢了,就不管正義了。他打住了一下,向全場從容問道,「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要我讀完麼?」那工人終於嘀咕著走了。──但是我知道的究竟太少,也許還是藏拙為佳。
寫這些篇雜記時,我還是抱著寫《歐遊雜記》的態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現。「身邊瑣事」還是沒有,浪漫的異域感也還是沒有。並不一定討厭這些。只因新到異國還摸不著頭腦,又不曾交往異國的朋友,身邊一些瑣事差不多都是國內帶去的,寫出來無非老調兒。異域感也不是沒有,只因已入中年,不夠浪漫的。為此只能老老實實寫出所見所聞,像新聞的報導一般;可是寫得太認真,又不能像新聞報導那麼輕快,真是無可如何的。遊記也許還是讓「我」出現,隨便些的好;但是我已經來不及了。但是這九篇裏寫活著的人的比較多些,如《乞丐》《耶誕節》《房東太太》,也許人情要比《歐遊雜記》裏多些罷。
這九篇裏除《公園》《加爾東尼市場》《房東太太》三篇外,都曾登在《中學生》雜誌上。那時開明書店就答應我出版,並且已經在隨排隨等了。記得「七七」前不久,開明的朋友還來信催我趕快完成這本書,說免得彼此損失。但是抗戰開始了,開明的印刷廠讓敵人的炮火毀了,那排好的《雜記》版也就跟著葬在灰裏了。直到前些日子,在舊書堆裏發現了這九篇稿子。這是抗戰那年從北平帶出來的,跟著我走了不少路,陪著我這幾年──有一篇已經殘缺了。我重讀這些文字,不免懷舊的感慨,又記起和開明的一段因緣,就交給開明印。承他們答應了,那殘缺的一篇並已由葉聖陶先生設法抄補,感謝之至!只可惜圖片印不出,恐怕更會顯出我文字的笨拙來,這是很遺憾的。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樹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來去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裡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又剩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歌聲
昨晚中西音樂歌舞大會裡「中西絲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彷彿一個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然灑在我臉上,引起潤澤、輕鬆的感覺。新鮮的微風吹動我的衣袂,像愛人的鼻息吹著我的手一樣。我立的一條白礬石的甬道上,經了那細雨,正如塗了一層薄薄的乳油;踏著只覺越發滑膩可愛了。
這是在花園裏。群花都還做她們的清夢。那微雨偷偷洗去她們的塵垢,她們的甜軟的光澤便自煥發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豔下,我能看到她們在有日光時所深藏著的恬靜的紅,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與綠。以前錦繡般在我眼前的,現在都帶了黯淡的顏色。─—是愁著芳春的銷歇麼?是感著勞春的困倦麼?
大約也因那濛濛的雨,園裏沒了濃郁的香氣。涓涓的東風只吹來一縷縷餓了似的花香;夾帶著些潮濕的草叢的氣息和泥土的滋味。園外田畝和沼澤裡,又時時送過些新插的秧,少壯的麥,和成陰的柳樹的清新的蒸氣。這些雖非甜美,卻能強烈地刺激我的鼻觀,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聽著;也用心唱著。我終於被一種健康的麻痺襲取了,於是為歌所有。此後只由歌獨自唱著,聽著,世界上便只有歌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