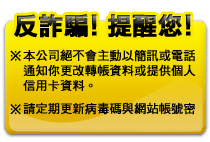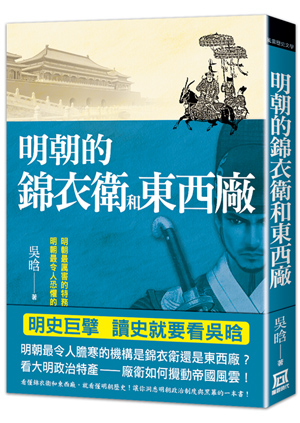
貪污腐敗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念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倖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越多。升官發財,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的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饑寒交迫的人民起來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污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污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爭。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地打擊。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的空印案,十八年(一三八五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傾家蕩產,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帳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准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錢穀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須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個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
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合情合理,方便省事。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朱元璋忽然發現了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用於別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成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辦法。但是案發後,正當胡惟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有一個老百姓拼著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未起作用,朱元璋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
郭桓官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產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朝廷宣布的罪狀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劃削殆盡」。這些記載雖然有些誇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舊地主階級分子被消滅的情況,則是無可置疑的。
這樣嚴重的打擊,當然會引起地主階級和官僚的恐慌及不滿,他們當然不敢申說買賣官糧這一嚴重犯法行為是合法的、應該的,只能指斥、攻擊、告發處理這個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一時議論沸騰,情勢嚴重。
朱元璋也覺得這個矛盾如繼續發展下去,對自己的統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詔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狀,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審法官也殺了,作為對地主階級和官僚們的讓步,結束了這件大案。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兩次大屠殺以外,還有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錄(甄別)天下官吏;十三年(一三八○年)連坐胡黨;十九年(一三八六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一三九○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計劃的誅殺。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凌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戴死罪和徒流罪辦事是朱元璋新創的辦法,有御史戴死罪,戴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創立這種辦法的主要原因是把這些官都殺了就沒有人替他辦事了,於是又判刑,又讓回去辦事,封建法紀確立了,各種事務工作也不致於因為缺官而廢弛。
凌遲是最野蠻、最殘酷的刑法。梟示也叫梟令,種誅就是族誅,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地殺。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腸,有剝皮,還有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的非刑。可見,朱元璋野蠻殘暴的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帝王。這種種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極度恐怖氣氛,人人提心吊膽。
用重刑懲治違法官僚,儘管殺死了幾萬人,效果還是不大。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朱元璋慨嘆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髮、紋身,罪之甚者歟!」
他沒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專制的寡頭獨裁政治,地主階級專政的殘酷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舞弊是分不開的,封建統治是以剝削人民為基礎的,不推翻封建統治、封建制度,單純地用嚴刑重罰,流血手段來根絕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誅殺以外,較輕的犯罪官員,罰做苦工。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謫發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
朝官被殺有記載可查的,有中書省左司都事張昶,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余愾,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御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御史王朴,員外郎張來碩,參議李飲冰,紀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寧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
茹太素性情剛直,愛說老實話,幾次因說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寫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朱元璋聽了也很感動。不多時他還是因事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究,勸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發揚朱學。朱元璋不理會,李仕魯著急,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朱元璋大怒,當時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御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是他寫的,做過禮部尚書,參加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因為起了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恨他:「自去爵祿之名,怪稱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又說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忘君爵而書耐久。」後借題發揮把他殺了。
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取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
朱元璋對內外官僚的殘酷誅殺和刑罰,引起了官僚集團的反對,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便有人抗議,說是殺得太多了,太過分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九年(一三七六年)葉伯巨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懼歟!
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唯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知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捨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捨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放肆!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朱元璋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
朱元璋晚年最喜歡的青年才子解縉,奉命說老實話,上萬言書,也說: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始終如一者也……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
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子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
話說得很露骨,分量很重,但是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於「臣下之乏忠良」,不是皇帝的本意,朱元璋讀了很舒服,連說:「才子!才子!」
在鞭笞、苦工、剝皮、挑筋以至抄家滅族的恐怖氣氛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官遠官,隨時隨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慌亂緊張、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有人實在受不了,只好辭官,回家做老百姓。可是這樣一來,又刺著朱元璋的痛處了,說這些人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將此種行為定為大不敬,非殺不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弄得官僚們「知懼而莫測其端」了。
也有個別得罪的官僚、貴族以裝瘋倖免的,一個是御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複訊,皇太子主張從寬。袁凱回報,朱元璋問他:「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誰不對,只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皇太子要赦免是慈心。」朱元璋大怒,認為袁凱兩面討好,耍滑頭,要不得。袁凱嚇得要死,怕被殺害,便假裝瘋癲。
朱元璋說瘋子是不怕痛的,叫人拿木鑽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齒,忍住不喊痛。回家後,自己用鐵鍊子鎖了脖子,蓬頭垢面,滿嘴瘋話。朱元璋還是不相信,派使者召他做官,袁凱瞪著眼對使者唱月兒高的曲子,爬到籬笆邊吃狗屎,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朱元璋才不追究。
這一回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凱知道皇帝要派人來偵察,預先叫人用炒麵拌糖稀,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大口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
另一個例子是外戚郭德成,郭寧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髮,朱元璋笑著說:「醉瘋漢,頭髮禿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郭德成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拉長臉,一聲不響。
郭德成酒醒後,知道闖了大禍,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朱元璋信以為真,告訴寧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個如此,真是瘋漢。」不再在意。黨案起後,郭德成居然漏網。
吳人嚴德珉由御史升左僉都御史,因病辭官,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到宣德時還很健朗。
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臺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來。御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臺長嚴德珉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著鋪蓋走了。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了什麼罪過,嚴德珉說了詳情,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裡連說:「聖恩!聖恩!」
民間流行著一個傳說,說是朱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墨跡還新鮮。朱元璋立刻派人搜索作畫題詩的人,已經不見了。這個傳說當然是虛構的,卻真實地反映了洪武朝官僚們對現實政治鬥爭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