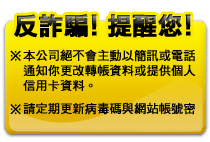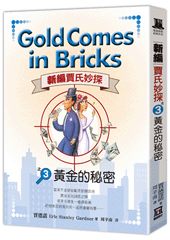
柯白莎深深歎口氣,把自己塞進一張可以摺疊的木椅子去,扶手兩側溢出來的是她多餘的脂肪。她點上一支菸,手指上的金鋼鑽,在照向鋪了榻榻米的高燈強光下,畫出了一個半圓的閃光來。比起其他地方沒有人,幽暗的健身房來,她的戒指有如太陽光下一滴海水。
那日本人,光著腳,穿了一套漂白了的粗麻裝,看向我,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冷得發抖。他給我的衣服太大了。裡面只穿短褲的我,覺得自己像裸體的,身上起了雞皮疙瘩。
「橋田,給他下點功夫。」白莎說。
大得出奇的健身房裡,只有我們三個人。那日本人用嘴唇強調地向我微笑,我看到他兩排潔白,不整齊的牙齒。無情的強光發自埋在飲馬水槽型,馬口鐵製成,高吊在罩子裡的幾個五百燭光燈泡,直接照我頭上。那日本人全身是結實的肌肉。他有動作時,日光曬黑的皮膚下,看得到肌肉在蠕動。
他看向白莎。他說:「第一課,不能操之過急,慢慢來。」
白莎猛抽了一口菸。她的眼光硬如鑽石。她說:「橋田,他是個聰明的小子。他學起來很快的,尤其花我鈔票的時候。我要他速成,我才不吃虧。」
橋田的眼光還是看著我。「柔道,」他用單調的聲音解釋給我聽。「是力的轉換,對方提供力,你改變他的方向。」
我看到他說了這句話後停了下來,知道該我點頭了,我就點點頭。
橋田自衣襟裡拿出一支短銃轉輪槍。鍍鎳都已經褪掉了,槍管也銹了。他打開圓筒給我看沒有裝子彈,是支空槍。
「對不起,」他說:「貴學生請把槍拿去,用右手拿著,舉槍,扣板機。快,請。」(『快』在前,『請』在後,係日語方式。)
我把槍拿到。
柯白莎臉上的表情有如她在墨西哥看鬥牛。
「快請。」橋田說。
我把槍舉起。
他輕輕伸個手出來輕蔑地把我的手推開。「請不要太慢。假裝我是大大的一個壞人。你舉槍。快!請,你扣扳機,在我動作之前。」
我記得我看過西部片,陰險的人都是在別人不注意的時間開槍的,也總是一面舉槍,一面就在扣板機了。這是一種扣一半撞針舉起,繼續扣下去撞針撞下的槍,我突然把槍舉向他,同時扣扳機。
橋田就站在我前面,是個大靶子,我幾乎可以確定槍裡如果有子彈,他一定會應聲倒地的。
突然,我發現橋田已不在前面,他已開始行動了,我試著用槍指向他行動的方向,但是他動似脫兔。
黃色強硬的手指一下扣住我的手腕。橋田既不在我正前,也不在我後面,他在我腋下,背部向著我。我的上臂在他肩上。他把我的右腕下壓,他的肩頭用大腿的力量上升壓住我腋窩,我的腿離開地面,上面的強光,地下的榻榻米互換位置。我感到自己在空中停留了幾秒鐘,一下被摔落到榻榻米上。
著地瞬間,我的胃不舒服得厲害。
我試著想站起來,但是肌肉不聽使喚,反倒使我想吐了。橋田低下身來,抓住我手腕和手臂把我一提,我像自榻榻米上被彈起一樣站了起來。他的牙齒一下全露了出來。槍在他身後地上。
「簡單就這樣。」他的日語式會話又出籠了。
柯白莎的戒指隨著她的手在動,鑽石閃光在亂射。
橋田抓住我肩頭,推我的背,把我右臂抬起。「就這樣,請。我來教你。」他把請加在最後,我知道一定是日語中的「苦得煞伊」了。
他大笑──神經質,無希望地笑。我也知道,強光下,廣大的場地中央,我站在那裡,身子彎曲,右臂前伸,右腕下垂,身子在前後搖晃。
橋田說:「現在你注意看,請。」
他慢慢分解動作地把身體移動,示範給我看,我一如在電視上看慢動作重播。他左膝微屈,重心移向左前到左臂,再升起來的時候,他身體移轉。他右手前移。他的手指漸漸扣住我右腕,左踝在榻榻米上旋轉。他的左肩頂上我右腋窩,手腕的力量加強。我右肘被扭到無法彎曲的位置,他加強壓力,把我整個上肢當一個槓桿。他加強壓力等我感到疼痛,不自覺雙腿又離了地。他把壓力放鬆,慢慢把我放下,站著對我笑。
「現在,你試試。」他說:「開始,慢一點,請。」
他站在我前面,右手向前伸出。
我用手抓向他手腕,他不耐地把我推開。「不要忘了左膝在先,學生,請。左膝先彎曲向前,同時出右手。第二步,旋轉手腕,足踝要同時,如此對方肘部就彎不起來。」
我又試。這一次比較好了一點。他點點頭,但是有點明顯的不太熱心。
「現在,試著對付槍,請。」
他拿槍在手,把手抬起用槍指向我,我記得出左腳,用右手快速抓向他手腕。我差兩寸沒有抓住,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他太講究禮貌,不好意思笑。如此對我而言更糟。
我聽到我自己衝出榻榻米舖的地方,光腳在健身房拍嗒拍嗒保持平衡的聲音。
橋田說。「抱歉,請。」他轉身。他眼睛斜著,瞇成一條線,看向已衝出強光,進入黑暗中的我。
這樣我看到了正在向前走,但仍在暗處的男人。那男人抽著一枝雪茄,帶了一副眼鏡,看得出眼珠是褐色的,年齡在四十歲左右。他的衣服裁製得很好,強調胸部的凸出和腹部的收縮。但是,即使如此,仍掩不住看得出他雙肩是陡削的,肚子大得像西瓜。
「你是柔道教練嗎?」他問。
橋田露出牙齒,走向前。
「我姓薄,薄好利。海富郎叫我來看你。我等你有空再聊好了。」
橋田把有力的手伸出來和他握手。「初見面。」他說:「高貴的朋友可以坐,請。」
橋田的動作是快如捷豹的。他抓起一張可以摺疊的帆布木椅,一下揮開,木椅發出聲音並有爆裂感。他把張開的木椅放在白莎的椅子邊上。「十五分鐘好嗎?」他問:「學生在上課。」
「沒問題。」薄好利說:「我等。」
橋田向白莎深深一鞠躬。他又向我鞠躬致歉。他再向薄好利鞠躬。他說:「再來試,請。」
我向已在白莎身旁坐下的薄好利看去。他也用好奇的眼光在看我。當著白莎的面受這種訓練已經不好受了,再加一個外人參觀,實在是無可忍受了。
「你先去辦事,」我對橋田說:「我來等好了。」
「你會受涼的、唐諾。」白莎警告道。
「不要,不要,你們教你們的。」薄好利把拿在手裡的帽子放在椅旁地上。「我一點也不急,我──也想看看。」
橋田面向我,牙齒軋礫磨出聲音來。「我們再試。」他拿起槍來。
我看到他不在意地抬手,我咬緊牙關,向前衝出,伸手抓住他手腕,我驚奇地發現這並不困難,我肩部頂向他腋窩,我把他上臂向下壓。
意想不到的奇蹟出現了。我知道橋田故意跳起來一點,但效果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他自我頭上翻過。我看到他雙腳自空中飛過,兩條腿在強光下形成陰影。他像隻貓在空中翻身,掙脫我的手,雙腳輕巧地落地,手槍落在地上。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有意脫手的。但是觀眾不知道。觀眾的興趣一點也沒有因為他故意的行動減弱。
白莎說:「嘿!小不點的學習能力真強!」
薄好利快速地看向柯白莎,又看向我,閃著欽佩的眼光。
「很好。」橋田說:「非常,非常好。」
我聽到白莎不在意地在告訴薄好利。「他是替我工作的。我開一個私家偵探社。這小不點有事無事常挨別人的揍。以拳擊言,他太輕了,我認為由日本人教他柔道,正好。」
薄好利轉頭以便好好看她一下。他只能見到白莎的側面。她正用冷而硬的眼光全神地在看我。
白莎全身都可以說是硬朗的。她個子大,都是肉,不過都是瘦肉。她粗脖闊肩,大胸,大臂,胃口也大。她不在乎自己體形,她愛吃。
「偵探,你說你是偵探?」薄好利問白莎。
橋田對我說:「我們現在來看我示範分解動作。」
柯白莎眼光仍看著我們。「是的──柯氏私家偵探社。在學柔道的是我部下,賴唐諾。」
「他替你做事?」薄好利問。
「是的。」
橋田自身上掏出一把橡皮製的假匕首。把刀柄向我遞來,叫我拿著。
「這傢伙是個小不點,但是他腦筋好得很,」白莎繼續對薄好利說:「你不會相信的,但是他還是個律師,領過執業熱照。他們把他踢出來,因為他告訴一個人,去做件謀殺案,可以保證無事。他有辦法一步一步去……」
橋田說:「用刀刺我,請。」
我抓緊刀子用力向前戳。橋田出擊,抓住我手腕和手背,不知如何我又飛上了天。
當我站起身來時,我聽到白莎在說:「──保證會滿意。很多偵探社不接離婚和政治案件。我只要有錢賺,什麼都接。我不在乎誰或辦什麼,鈔票第一。」
薄好利現在真的在仔細看她了。
「我想,我應該能相信你們工作能守密的囉?」薄問。
柯白莎對我在做什麼現在已經沒興趣了。「老天!當然。百分之百!你對我說任何事都不會傳出去。」
「建議精神要集中,請。」橋田說:「剛才這一跤摔得不好看,既已被摔出去,落地要用腳,馬上警備敵人第二次攻擊。」
柯白莎不知什麼時候已站起身走向門口。她連頭也不回,她說:「唐諾,快穿起衣服來,我們有案要辦了。」
我坐在辦公室外等著。我可以聽到柯白莎辦公室傳出來的低低交談聲。白莎在和顧客討論價格的時候,從不喜歡我在旁邊聽的。她給我月薪,而且相當刻薄,用最少代價搾取最多勞力。
二十分鐘後,她叫我過去。自她臉上,我知道討價還價後,對她很有利。薄好利坐在客戶椅上(這張椅子很不舒服,後來換掉了),他的身子接觸到椅子的只有兩點──頸子根部和褲後口袋。如此的坐姿使他胸部塌陷下去,頭頸又向前戳出。他這樣坐法才把肚子坐大,還是肚子大了,才如此坐的,我不知道。
白莎擠出笑容,甜蜜地說:「唐諾,你坐。」
我坐。
白莎戴了鑽戒的手,把一張支票裝進抽屜裡一個現鈔箱去,動作很快,我連看一眼支票上的數字都沒有機會。「是我來告訴他,」白莎問薄好利:「還是你來說?」
薄好利嘴裡有一支新雪茄。由於他頸子是向前彎著,所以他只能自眼鏡的上面看向我。本來在抽那支雪茄的菸灰落得他背心上斑斑點點。新的一支才開始抽,菸灰尚不多。「你來說。」他說。
白莎把一件複雜的事實,變成簡單的敘述:「薄好利是去年結的婚。薄佳樂是他第二任太太。薄先生第一次婚姻時有一位女兒,叫雅泰。前妻死後,她的一半財產歸了我們的當事人,薄好利先生。」白莎同時用手指向薄好利指一指,好像是一個老師在上課時指黑板上的一個數字給學生看。「另外一半,當然給了她女兒雅泰。」她看向薄好利說:「我記得你並沒有告訴我,這筆財產的數目。」
薄好利的眼珠子骨溜溜自眼鏡上面,從我看向她。「是的,我沒有說。」他說。說話的時候他沒有把雪茄從口上取下,菸灰掉了不少在他領帶上。
白莎用快快接下去說話掩住這一點窘態。「現任的薄太太以前也結過婚──前夫姓丁。兩人有個男孩,名叫丁洛白。這都是背景。由於媽媽再嫁,洛白覺得日子好過得很。薄先生,是嗎?」
「是的。」
「薄先生要他去工作,」白莎繼續道:「他就表示他的獨特態度,由於他『我為大』的人格……」
「他根本沒有人格,」薄好利插入道:「他也沒有任何經歷。有一些他媽媽的朋友,為了他和我有名義上父子的關係,把他介紹進一個公司。那孩子想有一天吃定我,門也沒有。」
「這一點你自己告訴唐諾吧。」白莎說。
薄好利把雪茄自口中取出。「沒收農場投資公司,是由兩個人在控制,蘇派克和卡伯納。我太太認識卡伯納很久了──在和我結婚之前。他們給小洛一個職位。三個月之後,就把他升為銷售部經理。又兩個月,董事會叫他做總經理。你自己想想,他們要的目標是我。」
「沒收農場?」我問。
「那是公司名稱。」
「做什麼生意的?」
「礦產,礦業開發,採礦。」
我看向他,他看向我。白莎把問題提出來:「沒收農場投資公司怎麼會和開礦搞在一起?」
薄好利坐在椅子中又陷了一點下去。「我怎麼會知道?我根本也不想知道小洛的工作。我也不要他管我的事。我要是一問他問題,早晚他會叫我買他股票。」
我拿出小本子,把薄好利提過的名字記下來,又加一行,訪問沒收農場投資公司。
薄好利看起來和他在健身房時完全不同。他又自眼鏡上溜著眼看我,我覺得他像一隻雙耳和下唇下垂的大猛犬被繫在鏈條上。他的眼睛在說,假如多給他鏈條兩尺的距離,他會在我腿上咬下一口。
「你想要我們幹什麼?」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