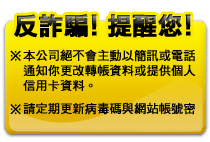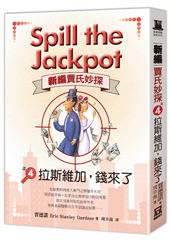
護士小姐說:「楊大夫希望你見病人之前先能見他一下。請你跟我來。」
她在前走,有韻律的腳步聲,和漿燙過的白制服沙沙聲,透散著專門職業的氣息。
「賴先生,」她通告說。
我走進辦公室,她把門自我後面關上。
楊大夫有薄得透明的鼻梁,細而透視力強的眼睛,看他臉我好像在看一條直線,兩邊各有一個黑點。
「賴唐諾先生?」他問。
「不敢當。」
長而冷的手指握住我手。他說:「請坐。」
我坐下同時說:「我的飛機四十七分鐘後起飛。」
「我會儘量簡短,你是來接柯白莎太太出院的?」
「是的。」
「她的情況你都清楚嗎?」
「不多。她感冒後轉成肺炎,洛杉磯的大夫建議她來這裡作長期休養。」
「他們告訴你原因嗎?」
「沒有。」
「你是她合夥人?」
「我是她僱員。」
「她主持一傢私家偵探社?」
「是的。」
「你現在全權在代理她的業務?」
「是的。」
「她對你有非常好的評介,賴先生。」他說:「十分信任。」
「從薪水上,不太看得出來。」
他笑笑:「我倒希望你能知道她的情況。我不想使她緊張所以沒有告訴她。最好你能請她洛杉磯的大夫告訴她。」
「她到底什麼情況?」
「你當然清楚她有多重?」
「不真正知道,她有一次告訴我,任何她吃下去的東西都會變成脂肪。她什麼不吃只喝水也會胖。」
楊大夫逐字嚴格地說:「不可能,她只是因消化機能良好,她──」
「把每一點食物都變為營養。」
「可以這麼說。」
「那就是白莎。」我說:「她就是這樣。」
他觀看我數秒鐘說:「我給她訂了一份嚴格的飲食單。」
「她不可能遵守的。」
「所以要請你來監督她。」
「我不可能監督她,再說我也忙不過來。」
「以體重來說,她已把自己弄到十分危險的情況了。」
「她不關心這件事。」我說:「她本來很重視體型。直到有一天發現她先生對她不忠實。於是她讓他有女朋友,而自己猛吃,至少這是她自己告訴我的故事。先生死後她照吃。」
「給她減肥已很成功。目前體重必須保持。絕對不能再肥,否則心臟會不勝負擔。要知每磅脂肪須多少微血管來供應血液。她以前就是循環不良才小病變大病的。」
「你有沒有和柯太太談過?」
「有。」
「她反應如何?」
我可以從他眼中見到憤慨的表情:「她叫我滾我的蛋!」
「正是她的口氣。」我說。
他按了一下鈴,護士立即開門。
「賴先生來見柯太太,她可以出院了。」楊大夫指示。
「是的,大夫。」
「費用都付了嗎?」我禮貌上應該問一下。想像中他們會回答收費單會寄去辦公室,再寄支票來結帳不遲。
大夫避開我視線說:「已妥協了。柯太太提了強力的抗議,所以費用我們已──妥協了。」
我跟隨護士經過一條長走廊,上了一層樓,她停在一扇門前。我把門推開。柯白莎說:「滾出去!費用已付清,再也不量體溫──喔!是唐諾,你來得正是時候。進來,進來,不要盡站在外面。把我行李拿著,早離開這鬼地方早好。全世界最──你怎麼啦?唐諾。」
我說:「我幾乎不認得你啦。」
「我自己也不認得啦。我病重的時候輕了不少。大夫不准我吃東西以免體重上升。昏他的頭,唐諾你知道我現在多重,只有一百六十磅啦。以前的衣服一件也不能穿了。」
「你看起來很棒。」
「少來!少來這鬼大夫那一套。一定是鬼大夫要你來拍我馬屁,又告訴你我心臟不勝負擔,是嗎?」
「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楊大夫那種剛出道的把戲,我要是看不透還能稱為偵探呀。我說等你來接我,他就問飛機什麼時候到,又對護士說你一到先要見你,都是一派胡言。你把我的業務弄得怎麼樣了?有賺錢嗎?最近我開支太大,公司一定要緊縮每一分開支。你知道所得稅徵得多兇?我同意愛國,但是全國軍備都要靠我來──」
我抓起行李說:「班機十點起飛,我有部計程車在等。」
「計程車!在等?!」
「是的。」
「你為什麼不早講。你看你在這裡嚼舌頭,計程錶在那裡滴嗒滴嗒吃我們錢,我的收支永遠不能平衡。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但你老以為鈔票是樹上長出來的,照你亂花的樣子看來,你──」
白莎大步跑出房間時,護士伸出她的手說:「再見,柯太太,祝你好運。」
「再見。」白莎沒回頭,一面回答一面加速在走廊上跑。
我說:「講好等候不要錢的。」
「喔,」她說,緩下腳步。
我們步下階梯,計程車駕駛代我們裝行李。
「機場?」他問。
「機場。」我說。
白莎向後靠在車座上:「區先生的案子怎麼樣了?」
「結案了。」
「結案了?你把目前我們唯一在手上的案子結案,我還賺什麼錢?」
「我們找到她,他付了獎金。」
「喔。」她說。
「我們有了另一件案子。」我說。
「什麼案子?」
「還不知道,一位華先生來信,希望今晚我們派人到拉斯維加斯和他見面。」
「有先匯錢來嗎?」
「沒有。」我答。
「你怎麼回他?」
「電告他我會去見他。」
「沒要他付定金?」
「沒有。我們反正要經過那裡,我可以留一晚,並不多花費什麼。」
「我知道,但是你本可先向這位花先生要點錢花花──」
「華先生。」
「好,不管他姓什麼。他想要什麼?」
「他沒說。」我從口袋裡拿出他的信:「這是他來信。看這信紙的材料,幾乎可以代替金屬做飛機外殼了。」
她看看那信紙信封說:「我跟你一起耽擱一天見見他。」
「不,你應該休息一、二個星期。」
「胡說,讓我自己來接頭。」
我什麼也沒說。
我們在起飛時間十五分鐘前到達機場。在候機室等候。過不多久,自東來的班機到達。擴音器宣佈西行旅客開始登機,白莎和我進入機艙。約有半打過境旅客早在機上未下機。白莎找座位坐下,長嘆一聲說:「我已經開始餓了。唐諾,跑回去給我買兩塊巧克力條。」
「不行,沒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