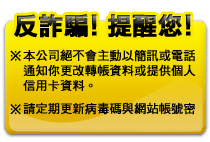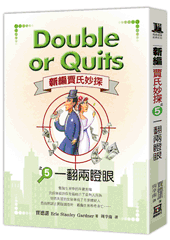
漲潮時間,釣魚專用的平底大駁船,懶懶地在水面上晃著。只有少數的釣魚竿,從不同方向,自船欄伸向海上。東方,日光才自加州海平面升起。被污染的海面有很多油漬,反射著才露面的陽光,使人眼睛刺痛。
柯白莎,無論體型或個性,都像一捆帶刺的鐵絲,坐在一張帆布導演椅中,雙足足跟翹在船沿上,手裡平穩地拿了一支魚竿。她閃閃發光的小豬眼,瞪住了她自己的釣線,跟住了閃閃發光的浮標。
她伸手到毛衣口袋中,取了支香菸,放到唇邊,兩眼沒有離開原來的目標。「有火柴嗎?」她問。
我把我的魚竿斜靠在欄杆上,用兩個膝蓋固定住,擦亮了火柴,用手兜著,送到她香菸上。
「謝謝。」她說,深深地吸了一口。
柯白莎曾經因為有病,把體重減到了一百六十磅。精力稍稍恢復,她開始釣魚。戶外運動使她健康進步,皮膚也曬紅一點。她還保持一百六十磅,只是多了些肌肉。
在我右側的男人,很厚,很重,呼吸的時候有點喘音。他說:「成績不太好。是嗎?」
「不太好。」
「你們來了一會兒吧?」
「嗯哼。」
「你們兩個是一起的?」
「是。」
「釣到什麼嗎?」
「有一些。」
大家無聲地釣了一會,他說:「我根本不在乎釣得上釣不上魚。跑出來輕鬆一下,呼吸一點帶鹽的新鮮空氣,逃避一陣文明都市的喧嘩,就值回票價。」
「嗯哼。」
「我最近每次聽到電話鈴聲,就好像大禍臨頭。」他笑笑,幾乎有點抱歉的樣子。他說:「其實說來就像昨天,當我剛開始執業時,我會不斷的盯著電話。好像看著電話,它響的機會會多一點似的。就好像你的──嗯──對不起。那位不是你太太吧?」
「不是。」
他說:「我本來想她是你的媽媽,但這個時代是很難說的。剛才說到她盯著看那釣魚線,就像以前我盯著看電話一樣,希望有點事發生。」
「律師嗎?」我問他。
「醫生。」
過了一下,他說:「我們醫生就是這樣,太注意別人的健康,就把自己的健康忽略了。這是慢性的折磨,早上開刀,巡視病人,下午門診,晚上出診。最不合理的就是半夜的急診,那些有錢人玩樂了一天,就等你上床了,才打電話來說他不舒服了。」
「你是出來度假?」
「不是。是溜號,我每個星期三總要想辦法溜號。」他猶豫了一下說:「沒有辦法,醫生囑咐。」
我看看他,他是超重不少。眼皮有點浮腫,所以每次垂下,要抬起就有點困難,從遠處看來他像一堆麵團,放在爐上等候發麵。
他說:「你的朋友,看起來蠻結實的。」
「沒錯,她是我老闆。」
「喔。」
白莎也許聽到,也許沒有聽到我們的談話。她看著她的釣線,像貓在守候老鼠洞一樣。白莎想要什麼東西,都是十分明顯的。目前她想要的是魚。
「你說你替她工作?」
「是的。」
他前額一皺,表示出他的疑惑。
「她主持一個偵探社,」我解釋,「柯氏私家偵探社。我們才辦完一件大案。偷一天閒,休假。」
白莎的竿尖向下一沉。她立即把右手握到她捲線機上。手上的鑽戒在日光下閃爍著。
「把你的線移開,」白莎對我說,「不要繞到一起去了。」
我把我的釣線向裡面拉。突然手一沉,我也上魚了。
「喔!」醫生說:「好極了。我來讓出空位來。」
他站起來,帶了釣竿沿船邊向外走。突然,他的釣竿一彎。我見到他的眼皮一翻,臉色也興奮起來。
我全神貫注自己的魚竿。左側白莎在鼓勵:「拉牠起來,唐諾,拉牠起來。」
我們三個人都在忙。藍藍的海水裡,偶然翻起銀白色的魚肚,是魚在掙扎。
白莎微仰上身,向後平衡自己。她雙臂上舉對付魚竿。一條大魚跳出水面。白莎利用牠出水的動力,順勢把牠帶起,拋進船欄。
大魚拋在甲板有如一袋濕透的麵粉。一秒鐘後牠用尾巴猛拍甲板。
醫生也把魚拖上了船。
我的魚脫鉤跑掉。
醫生笑著對白莎說:「你的比我的大多了。」
白莎說:「嗯哼。」
「可惜你的跑掉了。」醫生向我說。
白莎說:「唐諾不在乎。」
醫生好奇地看看我。我說:「我要的是空氣,運動,清閒。我辦起案子來一氣呵成,沒有休息時間。每結束件大案,希望輕鬆一下。」
「我也是。」醫生說。白莎看看他。
船上小吃攤飄出陣陣芥末香。醫生對白莎說:「要不要來個熱狗?」
「等一下,」她說,「魚等著上鉤呢。」她熟練地把魚從鉤上取下,串在繩上,掛上餌,把釣線拋出去。
我沒有再動手,只站著看他們釣魚。
不到半分鐘,白莎又釣到了一條。醫生也上鉤一條,但被脫逃。過一下,白莎上了條小魚,醫生上了條大魚。此後就沒有消息了。
「給你來個熱狗,怎麼樣?」醫生問。
白莎點點頭。
「你呢?」他問我。
「可以。」
「我去買。」醫生說:「我們慶祝一下,你繼續努力。請你照顧一下我的釣竿。」
我告訴他,我來負責照顧。
太陽已升過山頂,晨霧全消。岸邊,濱海公路上汽車移動清晰可見。
「他──什麼人?」白莎問,眼睛沒有離開釣線。
「一個工作忙,休閒少的醫生。他自己的醫生叫他要多休息。我想他另有所求。」
「是不是你告訴他我是誰了?」
「沒錯,他也許有興趣。」
「那樣好。」她說:「生意是隨時隨地會有的。」過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看他是另有所圖。」
醫生回來,帶了六個麵包夾熱狗,很多芥末和醃黃瓜。他開始津津有味地吃自己的第一個,手上最後那條大魚的魚鱗,沒有影響他的食慾。
他對白莎說:「我絕不會想到他是個偵探。我一直以為偵探要由粗壯的人來幹。」
「那你看走眼了,」白莎說,一面給了我滿意的一眨,「他像閃電一樣。而且我們這一行腦袋最重要。」
我看到浮腫的眼泡思索地看著我。眼皮慢慢閉上,又艱難地打開。
白莎說:「你要是有什麼心事,不要吞吞吐吐,說出來好了。」
他驚愕地看了她一下:「怎麼?為什麼,我沒有──」然後,他停止解釋,突然真正的笑出聲來。
「好!」他說:「算你厲害,我一直自誇病人不開口,我就能診斷出他三分病。沒想到自己被人看透了。你怎麼知道的?」
白莎說:「你做得太明顯了。唐諾說過我幹什麼的之後,你一直在觀察我。」
醫生把第二個熱狗抓在左手。他自口袋中拿出一個名片夾,很炫耀地拿出二張名片。給白莎一張,我一張。
我看看他的名片,放入口袋。得知他是戴希頓醫生。沒有預約他是不看病的。地址是近郊高級住宅區,辦公室在聯合醫務大樓。
白莎摸摸卡片上凸起的印刷字體,用手彈彈紙片看卡片質料的優劣。把卡片放進外套口袋。她說:「偵探社重要份子都在這裡,我是柯白莎,他是賴唐諾。你有什麼困難,說出來聽聽看。」
戴醫生說:「我的問題,實在是很簡單的。我遭小偷了。我希望能把失竊的東西弄回來。我來告訴你們實況,我在臥室的隔壁,佈置了一個舒適的書房。裡面放了不少淘汰下來的醫用儀器──X光機器,電療儀器,超音波,外行看起來還蠻像樣的。」
「你在書房工作?」白莎問。
他肚子有趣地抖動著。腫的眼皮閉起,張開的時間總比閉下久。「才不,」他說,「那些儀器是唬人道具。家中客人多,或是我不想陪他們時,我就說要做點研究工作,自己躲到書房去。我的客人都見過那房間,認為很了不起。我說過,外行看起來,很唬人的。」
「你在書房,做些什麼呢?」白莎問。
「房間的一角,是我選購的最舒服的椅子,」他說,「和最合宜的讀書燈。是我讀偵探小說的地方。」
白莎讚許地點點頭。
戴醫生繼續說:「週一晚上,我們有幾個特別無聊的客人。我躲到我的書房。客人走後,我太太上樓來──」
「你溜走,留下你太太招待無聊的客人,她不怪你?」
笑容自戴醫生臉上消失。「我太太沒有無聊的客人。」他說:「她喜歡熱鬧,她──她也以為我在工作。」
「你說她不知道那些儀器是假的?」
他猶豫著,像是在選擇合宜的回答。
「你不瞭解嗎?」我對白莎說:「戴醫生佈置那個書房,主要是騙騙她。」
戴醫生看著我說:「憑什麼你會這樣想?」
我說:「你太得意這件事了。每次想到這件事,你就會痴笑。好在沒有什麼大關係,你說你的好了。」
「很有見地的年輕人。」他對白莎說。
「向你說過的。」白莎澀澀地說:「星期一發生什麼了。」
「我太太戴著些首飾。我書房裡有一個牆上保險箱。」
「淘汰貨?像別的東西一樣,是假的?」白莎問。
「不,」他說,「保險箱可是如假包換的真貨。最新型式的。」
「發生什麼事啦?」
「太太給我她戴著的首飾,讓我放在保險箱中。」
「她常這樣做嗎?」
「沒有,星期一她說有點神經過敏,好像有事要發生。」
「這樣?」
「是的,後來首飾失竊了。」
「在你放進保險箱之前?」
「不是,是之後。我把首飾放進保險箱,去睡覺。昨天清早六點鐘我有電話,是一個盲腸炎穿孔。我趕去醫院開刀。又繼續本來排在早上的手術。」
「你太太通常都把首飾放那裡的?」
「大部分時間,是放在銀行裡租的保險櫃裡。十二點鐘之前,她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問我在我去門診前,能不能先開車回去一趟,為她開保險箱拿首飾。」
「她不知道保險箱號碼?」
戴醫生確信地說:「我是唯一知道怎麼開這個保險箱的人。」
「你怎麼辦?」
「辦公室護士接到電話後,轉告在醫院裡的我。我說我二點前後會開車回家一次。我後來一點鐘回去了。時間相當匆促。我除了喝咖啡外,早餐中餐都沒有吃。我跑進屋子,跑上二樓。」
「你太太呢?」
「她跟我一起進去書房。」
「你打開保險箱?」白莎問。
「是的。首飾不見了。」
「還有什麼同時失竊?」
他專心看著白莎的臉,有如白莎當初專心看著釣魚線相似:「沒有,只失竊了那一批首飾。本來保險箱裡也沒有太多東西。一、二本我留著急用的旅行支票。一些我對腎臟炎研究的報告。」
「你打開保險箱的時候,你太太,在哪裡?」
「她站在書房門口。」
「會不會你放進首飾後,保險箱門沒有關好?」
他說:「不可能。絕無可能。」
「保險箱沒有被人弄壞吧。」
「沒有。開保險箱的人,一定有正確的密碼。」
「怎麼會?」
「這就是我不懂的地方。」
白莎問:「有什麼人能──」
「我們知道什麼人做的,」他說,「我的意思是──我們知道是什麼人做的。」
「什麼人?」
「一個年輕女郎,姓史,」他說,「史娜莉小姐,我太太的秘書。」
「怎麼知道是她?」
戴醫生說:「有的時候,人會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我打開保險箱還以為自己在做夢。我太太問了許多問題。才使我知道這是真的,是我把首飾放進保險箱,而後轉動號碼盤的。」
「跟姓史的女郎有什麼關聯?」
「我太太把史小姐叫來,請她立即報警。」
「之後呢?」
「一小時之後,警察沒有來。我太太要知道為什麼警察遲遲不來。她再叫史小姐。史小姐失蹤了。她根本沒有通知警察。史小姐也多了一小時逃亡時間。」
「又之後呢?」
「之後警察來了。他們在保險箱上找指紋。他們發現做案後,有人用一塊有油的布擦抹過保險箱。在史小姐房間,一個空冷霜罐裡,他們找到了那塊抹布。」
「同一塊布?」我問。
「他們有辦法證明這是同一塊布。有一種特殊廠牌的擦槍油在這塊布上,和保險箱上留下的油相同。用了一半的擦槍油,也連瓶在史小姐房內。一切顯示緊急潛逃。史小姐什麼也沒帶走,化妝品,甚至牙刷。她是空手走的。」
「警察沒能找到她?」白莎問。
「還沒。」
「你要我們做什麼?」
他轉頭望向海洋說:「遇見你們之前,我並沒有想要做什麼事。但是,假如你們能在警察找到史小姐之前,先一步找到她,對她說如果她把失竊的東西退回我,我就既往不咎。我會付你們一筆可觀的費用。」
「你說你不準備控告她。」白莎問。
「我不告她。」他說:「我還準備給她點現鈔獎金。」
「多少?」
「一千元。」
他站在搖晃的甲板上,眼望外海,等著白莎回音。
我知道白莎在想什麼。她希望自己完全不出聲,能使醫生回頭看她,她再發動問題:「我們又有多少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