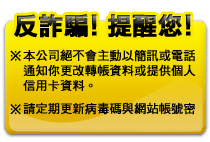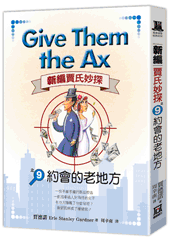
我跨出電梯,開始步向走道。熟悉的環境使我回想起第一次我來到這條走道的境遇。那一次我是來求職。
在那時,門上漆的字是「柯氏私家偵探社」。現在──一九四四年,門上漆的是「柯賴二氏私家偵探社」。左下方又漆著較小的「柯氏」,右下方則是「賴唐諾」。柯氏代表柯白莎。她是我合夥人,不願漆上全名,為的是免得解釋女人做這一行的許多問題。至於我的名字仍在門上,更使我確定回來是絕對值得的。
我推開門進去。
卜愛茜正在敲打打字機的鍵盤。她轉頭自肩向上望,訓練有素的微笑掛到臉上,任何一位來找私家偵探緊張的顧客,都會因為這種歡迎的態度安下心來。
她看到我,表情突然消失,兩隻眼睛突然睜大。
「唐諾!」
「哈囉,愛茜。」
「唐諾,老天,真高興見你。從哪裡回來?」
「南太平洋,還有許多許多其他地方。」
「你可以留──你什麼時候還要走?」
「不回去了。」
「真的不再回去了?」她問。
「可能不需要了。六個月之後我還需要做次體檢。」
「出了什麼事?」
「昆蟲──熱帶昆蟲。休息一回也不錯。回到清涼的氣候,不必整天緊張。白莎在裡面?」我把頭向裡面門上一比,門的玻璃上漆著「柯氏,私人辦公室」。
愛茜點點頭。
「混得怎麼樣?」
「老樣子。」
「體重呢?」
「仍舊保持一百六十五磅,還像一捆帶刺的鐵絲網。」
「有錢賺嗎?」
「有一陣子。但是後來她變得墨守成規,最近一陣都不太好。你最好是自己問她。」
「我離開這段時間,你一直坐在這裡打字嗎?」
她笑道:「沒有,當然沒有。」
「什麼意思?」
「每天只有做八小時。」
「看來也是墨守成規。我還以為你會辭職去兵工廠工作報國。」
「我的信收到了嗎?」
「信上沒有說還替我們工作呀。」
「我認為不必提這件事。」
「為什麼?」
她避開我眼睛:「我也不知道,說是對戰爭的貢獻吧。」
「忠於職守嗯?」
「忠於職位倒不見得。」她說:「守──倒是有一點,唐諾,你在外面打仗,我希望做點事『守住』你的事業呀!」
內辦公室呼叫鈴聲響起。
愛茜把桌上話機拿起,壓下通白莎辦公室的按鈕,說道:「什麼吩咐,柯太太?」
白莎發怒的聲音可以把電線燒熔。連我坐的地方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自話機發出的聲音說:「愛茜,我告訴你過多少次,和客戶講話,只要弄清楚他們想要什麼,立刻由我接見。一切的細節都由我來說明。」
「這不是客戶呀,柯太太。」
「是什麼人?」
「一──一個朋友。」
白莎的聲音一下升高了八度:「老天!我付你薪水是為了讓你在辦公室開聯誼晚會呀?老天!一個朋友……一個……你看著,我馬上給他好看!」
白莎那邊把話機摔下的聲音,不經話機,從關著的辦公室門都聽得清清楚楚。我們聽到兩下快步的聲音,辦公室門突然拉開,白莎已站在門檻上,發光的兩隻小眼充滿怒意,她的大下巴向前戳出。
她匆忙地向我所在方位看了一下,慢慢的向我邁步,有如一艘戰艦準備對付一隻潛水艇。
走到一半,她的眼睛終於通知了她氣瘋了的頭腦。
「嘎!是你這個小混蛋!」她說,兩隻腳凍住在地上。
這一刻她是真心十分喜歡看到我的。但是她立即控制自己,她不要任何人知道她心意。她轉向愛茜說:「什麼混蛋理由你不通知我?」
愛茜嚴肅地說:「我正要告訴你,柯太太,可是你把電話掛了。我要告訴你──」
「嘿!」白莎用鼻子發音使她停止說下去。然後轉向我說:「你回來也不先送個電報。」
我用唯一能使她產生反應的理由辯白:「電報要花錢。」
即使這樣還是沒有打動她的心:「你可以送個交際電報呀,那種電報文字固定,收費低廉。像這樣突然闖回來──」
柯白莎突然把話煞住,眼睛盯在通走道門的磨砂玻璃上。
一位女性的頭和肩的影子映在玻璃上,時髦,嬌瘦,一看即知年輕。也許是因為她站立的位置,也許是習慣的格調,她的頭稍稍側向一側,看起來更為俏麗。
白莎輕輕呧咕著:「豈有此理!顧客每次來時我都在外面一間,看起來那麼不正經,好像我們生意很差似的。」她一把攫起愛茜桌上一堆打好字的紙,裝做公事很忙的樣子,翻動著。
但是門外的人沒有進來。
足足有幾秒鐘的時間影子映在磨砂玻璃上,對我們來說時間停留了好像幾分鐘。突然影子決定不進來,向走道後端走下去。
白莎把那堆紙重重摔回桌上。「就是這樣。」她說:「最近我們的生意就是這樣。這個可惡的小娼婦可能去下面環美偵探社吐她的苦水去了。」
我說:「樂觀點,白莎。她可能緊張了一點,等一下會回來的。」
「好吧。」白莎輕蔑地說:「這地方風水不合她的口味。本來要進來,又不進來了。完全因為聽起來不像一個辦公室。愛茜,你回去打你的字。唐諾,你到裡面來。愛茜,你給我記住,要是她進來,她會很緊張。這種典型的顧客不會等候,她會突然說忘了什麼東西,站起來就走。那就再也見不到她了。記住她在頭髮的一側帶了一頂小帽子,她──」
「她的影子我看得非常清楚。」愛茜說。
「好,她一進來立即通知我。不要耽擱。立即用電話。要知道我總不能像寶斗里一樣在門口拉顧客。再想想也實在怪,要想做件事,為什麼不就去做呢?反反覆覆,像那女人一樣。其實我又何嘗不這樣,我應該開門拉她進來的。唐諾,我們進去,好讓愛茜打字。」
卜愛茜很快地給我一個微笑,充滿趣味的成份。回去就開始機關槍式的打字。
柯白莎把她大而健壯的手放在我臂彎中說:「走,告訴白莎當兵什麼滋味。」
我們進了白莎私人辦公室。白莎繞過大的辦公桌,把自己一下塞在那隻會吱咯叫的迴轉椅中。我坐在一張沙發高背椅的把手上。
白莎仔細看我一遍說:「你強健多了。」
「我有一段時間比現在更要強健。」
「現在多重?」
「一百三十五磅。」
「好像高了一點。」
「沒有,只是他們使我站的方法改變了。」
靜寂了一陣。白莎一隻耳朵注意著外間有無聲息。卜愛茜打字的聲音沒有暫停的樣子。
「生意不太好?」我問。
「差極了。」白莎咕嚕著。
「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你來這裡之前,我有不少瑣屑無足輕重的案子可以虛度時光。小的跟蹤案子,離婚案子這一類的,大多是家庭不和,別的公司不要的案件。而後『你』來了。一下子你給我大大的改變──更多的錢,更多的冒險,更多的興奮,更多顧客──而後你自己要去海軍當什麼兵,有一陣子我維持得還可以。然後不知怎麼了,我已有一年沒有值得一顧的案子了。」
「什麼原因?顧客都不來了嗎?」
「他們有來。」白莎說:「但是我不夠說動他們。他們不肯聽我的方法,我又不會你的方法。我是個四不像。」
「什麼意思你不會我的方法?」
「看那張你坐著的椅子,」她說:「就是個好例子。」
「什麼意思?」
「你做了我的合夥人之後,你狠得下心花一百二十五元買這張椅子。你的理論是客人坐立不安時,不可能贏得他們信心。而他們不舒服的話,也不能告訴你實況。你讓客戶坐在那張舒服的沙發椅裡,讓他們自以為在世界屋脊上睡在一張羽毛床上。他們向後一躺就開始說話。」
「倒是真的,他們會有信心和開口。」
「對你很靈,輪到我來就不靈了。」
「也許你沒能使他們感到舒服。」
白莎生氣地說:「我還要怎樣使他們舒服?我已經付了一百二十五元買張椅子給他們舒服。假如你想我浪費一百二十五元,另外還要──」
她說到一半突然停下。
我靜聽,什麼也聽不到。突然明白,愛茜不在打字。
一會兒之後,白莎桌上電話響起。
白莎把話機搶起,小心地說:「嗯。」而後輕輕地說:「是那個女人……是的?她姓什麼?……好,請她進來。」
白莎掛上電話,對我說:「離開這張椅子,她來了。」
「什麼人?」
「她的名字叫許嬌雅。馬上進來。她──」
卜愛茜開門,用特別通融的語氣說:「柯太太即刻可以見你。」
許嬌雅大概一百一十四磅,並不像從門上影子估計那麼年輕,應該是三十一、二歲,頭也沒有側向一邊。門上影子看到頭彎的原因,一定是因為她在門外側聽。
柯白莎對她微笑,用滴得出蜜糖的聲音說:「許小姐請坐。」
許小姐看看我。
她有深而有感情的眼珠,厚唇,高額,光滑橄欖色皮膚,非常深色的頭髮。她看我的樣子,就像要立即轉向逃跑。
白莎急急地說:「這是賴唐諾,我的合夥人。」
許小姐說:「喔!」
「進來,」白莎邀請著:「許小姐,你可以坐那張椅子。」
她猶豫著。
我深深的打了一個呵欠,一點也沒有意思要掩飾,自口袋拿出一本記事本來,隨意地說道:「那我就去做剛才我們討論的事,要不然──」我好像突然想起,轉向許小姐加上一句:「也許許小姐要我也在這裡聽你的事?」
我儘量使聲音有厭倦的樣子,好像多一件案子就加多一件雜務。我聽到白莎噎氣的聲音,好像要開口,但是許嬌雅向我笑著說:「我想我要你也坐下聽聽。」走向沙發椅,坐了下來。
白莎滿臉春風:「可以可以,許小姐,你說。」
「我要有人幫忙。」
「我們就是幫人家忙的。」
她把皮包打玩了一會,把膝蓋翹在一起,小心地把裙子弄整齊,雙眼避免看白莎。
她有雙美腿。
白莎熱情地說:「我們可以幫──」
嬌雅急急避開她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