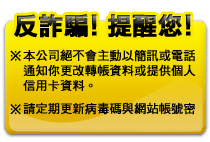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題辭〉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裡,編完那年那時為止的雜感集後,寫在末尾的,現在便取來作為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集的題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魯迅校訖記
※〈黃花節的雜感〉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裡「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崗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只得查《辭源》。書裡面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崗。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於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於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
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裡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裡,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弔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
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為著後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髮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意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
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彷彿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慄慄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譚》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彷彿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
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裡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
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閒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
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
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只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時代的文學〉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
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裡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
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
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裡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
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麼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牠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
牠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牠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
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
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裡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
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
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絕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