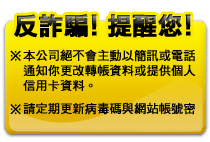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1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
古話裡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蹠見了,卻道可以黏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鳳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樑,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於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糊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撿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為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夜頌〉
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閒者,不能戰鬥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裡。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陰裡,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於佛畫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閣閣的走得很起勁,但鼻尖也閃爍著一點油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假如長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將使她碰著「沒落」的命運。一大排關著的店舖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緩開足的馬力,吐一口氣,這時之覺得沁人心脾的夜裡的拂拂的涼風。
愛夜的人和摩登女郎,於是同時領受了夜所給與的恩惠。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面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鬧,喧囂。而高牆後面,大廈中間,深閨裡,黑獄裡,客室裡,秘密機關裡,卻依然瀰漫著驚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六月八日。
〈推〉 豐之餘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絕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
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裡。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舊曆端午,在一家戲場裡,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啊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
「啊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