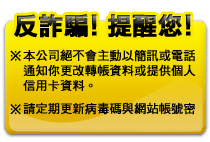流轉北大、南大、清華 (2005.01.19)
十五日由北京返台北。默念此半年行止,深覺有趣:
上半年在北大客座,兼往南京師大擔任講座教授,年後還要去清華。這三個地方串起來,竟默符民國以來文化發展之軌跡,實在太奇妙了。
民初五四運動的大本營在北京大學,這是不用再介紹的,其時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三年間。
一九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制,成為東南大學。即以南師及東南大學人馬,如梅光迪、胡先驌、柳詒徵、吳宓、劉伯明等,成立《學衡》雜誌,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成為對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批評者。梁實秋讀清華時,因赴東南大學參訪,結識了吳宓等人,返校後即在《清華周刊》上撰文稱揚《學衡》。而隨即吳宓也轉到清華來任教,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東南大學一批學生,如陳寅恪的助手浦江青、王國維的助手趙萬里,也都轉到了清華。所以《學衡》後期的撰稿群,以清華與南師改制後的東南大學為主。
這批學者,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與北大《新青年》所代表的激進文化改革派壁壘彷彿互異,其實《學衡》作者中如陳寅恪、湯用彤、向達、賀麟、張蔭麟,都與胡適或北大關係密切。現在的北大,經過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把原先在清華的馮友蘭等人都併入了北大,其間壁壘就更不分明了。
錢穆、馮友蘭在《學衡》時,胡適曾在日記中批評道:「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過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可是不旋踵而錢穆入了北大,馮友蘭隨後亦成為北大一塊招牌,故反動不反動,實在難說;北大、清華、南師這三地學人之交流轉輪,亦非保守激進等標籤所能涵括。而北大、清華、南師這三校恰好也是新文化運動以後整個文化發展的焦點。
我這趟赴大陸教書,亦如前輩學人般,流轉於這三校之間,感覺當然十分奇特。
兼融中西清華園 (2005.02.17)
由香港轉抵北京時,大雪甫過,滿地積雪猶未化也。驅車赴清華,稍事安頓,王小盾兄即來接待。縱酒傾談,踏雪而返。我準備在北京恢復「國際佛學研究中心」。小盾精研文學與音樂之關係,故略詢發展此一課題之可能性如何。
佛研中心,昔係由靈鷲山支持,發行國際佛學研究及國際佛學譯叢,且開設藏文巴利文班,如昭慧等皆曾在彼處聽課。於十六年前,在台灣,不啻於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在我去陸委會任職時,該中心也未停辦,直到我應星雲之請,籌辦佛光大學時才不得不離開。當時心道法師還來我家,勸我勿去佛光山,仍替他辦佛研中心及宗教博物館。我沒答應,只幫他維持了一段時期的佛研中心,還推展了新興宗教研究等項目。如今回首,殆若夢然。
今年除夕,心道法師來電,邀去靈鷲山度歲。我於十四日上午與林明昌同去。明昌曩時亦曾任該中心副主任,但未去該山均已十餘年了。山上海霧天風,猶如昔日。
十七日生安鋒來,送了一冊他新出版的《霍米巴巴》。
巴巴名氣甚大,但中文世界相關譯述卻極少,安鋒博士論文應儘早出版才是,此書僅小試牛刀耳。他又替我買了兩輛腳踏車,一同騎去熙春園午餐,王寧、高旭東、羅立勝都來了,聊起今年要辦紀念清華國學院八十年的活動,均有些感慨。
清華當然是洋派的學校,跟北大不同。北大原本是吳汝倫辦的,因此校內多桐城耆宿。後來一變而成激進派之大本營,痛批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林紓、林損等人相繼離開,以留日學生,包括章太炎、錢玄同、魯迅等人之影響力較大。清華則多是留歐美的。但這些歐美留學生對中西文化之態度反不像激進者那麼決絕,大抵比較屬於兼通交融性質,對傳統文化反而比較抱持溫情。因此像《學衡》派,雖創辦於南方,其大本營實在清華。講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吳宓、梁實秋也都在清華。國學院辦在這個洋學堂中,亦可見其學風之一斑。當時幾大導師,除梁啟超外,都有西學的背景,王國維鑽研康德、叔本華,陳寅恪採西方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且深入西方漢學之語言方法傳統,趙元任更不用說了。國學院之外,如聞一多、陳夢家也一樣治國學,例如甲骨、金文、神話、易經、尚書等,均可見兼攝中西,乃彼時風氣。葉公超剛返國時,因只通西洋文學,國學根柢不夠好,還被譏笑了一陣。待他能談點中國學問了,眾人才覺得他也是「我輩中人」。
這種現象,其實甚怪。不太懂西方的人拚命說要西化;比較瞭解西方的,則主張「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沈」(朱熹語),他們所認識的西方也不一樣。前者所知之西方,較像西方的東方主義者所謂的東方那樣,是個「想像的他者」。以這種想像來迫促中國改革,要求中國走上或變成那樣的想像之西方時,碰到清華這批留學生回來大潑冷水,說西方並不是這個樣兒,竟兀自惱怒了起來,痛詬諸君「保守」,豈非笑話?可惜在五四及以後那幾十年裡,整體風氣便是如此。說起來,大概只能歸於氣數罷!
當然,出現這種結果也是必然的。
因為根據想像來革命,遠比真正兼通中西容易得多,既便趨附,又能安頓急盼改革的熱情,比起冷靜地坐在書齋裡剖析中西、會通古今更能號召群眾,是無疑的。
可是在革命熱情燒退了以後,這種文化態度的價值就彰顯了。大陸這些年重新評價陳寅恪、梁實秋、吳宓等人,就有這個意味。我自己也比較認同這種態度。但我的情形又不一樣,我是由國粹派逐漸轉變的。
在我高中大學時期,為了把自己造就為一位國粹派,我可是耗盡了氣力,終於學會了做一名傳統文人、傳統經學家的全部技能,也養成了所有的脾性。我以此自豪,但爾後卻頗以此後悔。因為若我不那麼急著丟掉英文,我就可以瞭解更多西方的東西,觸類而長,對我的學問,定能大有裨益。往事不堪回首,與王寧、生安鋒等談起來,感慨自然也就多了。高旭東還問我出身到底是中文系抑或外文系呢,真是的!
夜小雪。出去買點文具,衣上撲滿了,如一粒粒碎鑽,沾了一頭一臉。
重讀姚際恆 (2005.02.18)
雪後大寒。出往藍旗營購下周往南京之火車票,凍得齜牙咧嘴,還是回家閉門看書為妙。
書是彭林先生送來借我讀的《姚際恆著作集》六大冊。姚氏著作多不傳,民國初年,經顧頡剛等人之提倡,才逐漸被人搜輯出來,中研院文哲所將之點校集編成這套著作集,有功士林,自不待言。住在這兒,能讀到台灣友人編的這部書,感覺更是奇特。
姚氏之學,被顧頡剛等人看重,是他的辨偽。顧氏讀他書時,還是借來手抄的呢!其《古今偽書考》後來增補訂正者甚多,亦最為世所知。其實整個姚氏經學也都在辨偽,例如說《禮記》,謂〈明堂位〉為新莽時人作,〈喪服大傳〉為漢儒作,〈學記〉乃諸子書,〈樂記〉乃武帝時人湊集而成,〈祭法〉亦漢人作,〈祭義〉則秦人筆,〈哀公問〉為孔門弟子推演之詞,〈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禮運〉多老莊之徒偽託……。斥〈中庸〉為禪學,尤可見其辨偽之旨。論《春秋》則棄傳以存經,不信「例」,謂例之說起於杜預。這些說法,在打破聖經賢傳的權威方面,頗具意義,但若評考其是非,則多可商榷。凡例之說,孫子兵法就有,出土郭店楚簡中亦可見此體制,非盡杜撰。先秦古書,皆經漢人隸定,據其文句以說真偽,實在也是困難重重。且以後代已定型的學派區分或觀念去看古人,古人古書不合我這個定型的看法,不思檢討自己的思想模套,反而說凡古人不合於我這個套子的就全是偽做,不是個大顛倒、大笑話嗎?
舉個例子。〈檀弓〉上篇:「公叔木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主張昭大功;「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則說:「魯人則為之齊衰」,建議採齊衰服制。這是女人在死了丈夫後改嫁才有的情況,談同母異父兄弟間如何穿喪服。可是姚際恆認為女人改嫁,「今世委巷間有之,若士大夫家自無此」。故改嫁以後發生的禮儀問題,均是失禮之禮,「失禮之禮何足為問」,孔門弟子居然還去討論它,他覺得甚怪。據子夏的說法看,魯俗對此已有限制,則是改嫁者甚是普遍,他覺得更怪。這不是少見多怪嗎?女人不改嫁為貴,乃明清風氣,執後世之俗,詫古人之風,豈不謬哉?
《古今偽書考》顧實說它曾「大為流行,各大學各高中學,咸油印發布,莘莘學子,幾於人手一編」。其實亦疏略。姚氏之目錄學本來大成問題,故其間多不可究詰。如以《麻衣正易心法》《孔子家語》入經部,《葬禮》《神異經》《十淵記》《杜律虞注》等入子部,都像顧頡剛說他把《忠經》列入經部,《天祿閣外史》列入史部一樣,是只憑書名去判斷,並沒仔細看過原書。如此辨偽,怎麼辨呢?
可是姚際恆自己並不覺悟他不懂目錄學,他反而喜治目錄學,今存《好古堂書目》《好古堂藏書畫記》《續收書畫奇物記》均是。柳詒徵跋《好古堂書目》甚推崇其於四部之外別立叢書之濫觴,卻未指出其中的錯誤。實則姚書之誤很不少。例如《墨池編》是談書法藝術的,不應列入小學類,《詩韻》數種,同樣也應列入文學而非小學,正如《廿一史彈詞》只是文學,不能編入編年史類,《搜神記》《搜神後記》列入集古類,亦不妥。《山海經》入方物而非地理、非小說;地理類收《新安文獻志》《炎檄記聞》;《水東日記》《日知錄》列雜家;《陽宅奧訣直指》《堪輿宗指》入天文家,亦皆可商。
雖然如此,姚氏的目錄也並非毫無足取,柳先生說他:「書之分類雖亦襲四部通例,而子目多特創,如史部有器用、蟲魚、方物、川瀆,皆別為品題,異於他目」。這其實就是一種專門書目。姚氏對目錄學並不在行,所以反而能亂搞出這些不傳統的目錄來。
現在看,這種東西反而有價值,怎麼說呢?一、我國的書目,多半只是工具性的,歷來甚少書目作者,不比歐洲,像迪柏丁(Thomas Frognall Dibdin, 1776-1847)寫了《史賓塞藏書目錄》《十日談書目解題》《法德訪古覓奇之旅》那樣的書目作家,少之又少。二、書目太過定型化,基本上就是四分法與七分法,外加佛道二種,很少時代性或專題性書目。所謂時代性,例如波拉德(Graham Pollard,1903-1976)《十九世紀小冊子類型調查》,另一位波拉德(Alfred William Pollard, 1859-1944)的《早期繪本書》《一四七五年到一六四○年於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印行的書籍簡目》均屬此,我國只有依附於諸史藝文志底下的時代性書目,非常單調。專題性書目則如後一位波拉德編的《莎士比亞四開本普查》。外國許多藏書家會以專題方式蒐集資料,如一九二二年美國藝術家協會進行拍賣的蘇珊.閔(Susan Minns)就專收跟死亡有關的書籍、畫作、藏書票、錢幣等;創立紐約圖像同好會的安德魯斯(Andrew),亦以抄繪本古籍、地圖、畫片、裝幀本、插圖本為收集對象,我們大概頂多只有專收北宋版元版的。專題書目是晚近的事,故姚際恆倒成了個先驅。
由書目看,中國人每自詡印刷術發明最早,典籍之豐亦舉世無匹,可是對書之蒐藏與編目,似仍有比不上西洋的地方。西方有些東西也是我們沒有的,如前文提到的拍賣會,即為一例。沒有拍賣會,自然也就沒有「拍賣目錄」和「交易帳」。由於書沒有此類公開拍售轉讓之網絡,同時也就沒有交換圖書、討論閱讀的「讀書俱樂部」。又由於特重文字,書之插畫配圖極不經意。除小說戲曲等通俗書刊外,正經典冊基本上也都不配圖,因此裝幀型式亦較呆板,材質及版型上缺乏變化。這些,都是今日治中國書目之學者所該知道的。
整體說來,姚際恆最好的作品,恐怕還是《好古堂家藏書畫記》,這實在與他在經學辨偽方面的聲名不符。首先,好古之堂號,便與他考古不佞的態度頗有差距;賞鑑書畫,附及繡像、刻絲、鐫印、硯石、研山、石屏、古琴、香盒、古墨、舊紙,亦顯一文士氣,而非經生之態度。在賞鑑這些藝術品時,他的趣味和文藝知識,也比談經學時可愛得多。在那麼嚴格分判老莊佛禪與儒家界限的經生姚際恆那兒,絕對不能發現他竟這麼喜歡佛道教的寫經,先後收藏了元僧血書法華經、吳鎮草書心經、文徵明楷書金剛經、董其昌寫盂蘭盆經等。據他說,在杭州得到血書法華經,曾為作贊語六萬多字,後來又作一贊說:「偉哉大雄尊,發此真空理」,則不惟賞其藝妙,亦贊其理高。足見一個人往往是複雜的,只從勇於辨偽的經學家一個角度去看,殊未能真正瞭解他。民國以來被重新認識的姚際恆,其實尚待後人重新去瞭解他。
夜看電視,杭州劇團演新排大戲「蘇東坡」,啼笑皆非。全劇大肆採用舞台劇形式,服裝、動作、化粧,不倫不類。劇情尤荒謬,云東坡在杭,創東坡全宴,包括麻辣燙、西湖醋魚、東坡肉等,且有東坡酒。然而,東坡根本不能飲,略飲即醉,故自製東坡酒,極淡,友人喝之,以為是惠山泉。今乃以東坡創製了什麼名酒;辣椒於十六世紀才傳入中國,麻辣更非浙江能有的口味,今胡亂編排一氣,乃是與古人作要。說東坡在西湖修了蘇堤,故被貶去海南修海堤,更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