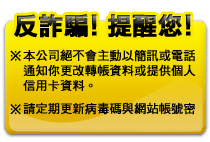割緣【作者限量簽名書】書衣收藏版

他和她坐車回到小木樓,彼此都談的是別後的話,一些生活上很平常的言語,直到女孩吃過飯,她才主動提到他們自己的事情。
「我母親是個很迷信的女人,」她說:「我說很迷信,並不意指她比一般老年人特別到哪裏,你知道,上一輩人裏面,有很多人都有若干忌諱,比如說我們吃飯拿筷子,我母親便會叫我不要抓得太高,說是女孩筷子抓得高,日後一定嫁得遠。」
「這一點,我很明白。」葛德點頭說:「在我的老家,也有同樣的習俗,迷信意味很濃的習俗,由於當時的交通情形不發達,女兒出嫁,通常不會嫁到遠方外地去;做父母的,不論迷信不迷信,總認為女兒嫁在家裏附近,回娘家走親戚方便,嫁了也像在家一樣。如果嫁給外地人,總有一天會被帶走,千里迢迢的,甭說走動不便,有時連音訊都斷絕了,那樣,嫁女兒等於丟了女兒一樣,即使男方家境好,他們也不會願意。這倒不是迷信不迷信的問題,這該算是人之常情。」
「其實,如今這種情形,已經改變了。」女孩說:「管他嫁在南,嫁在北,都是當天就到的地方。實在嫁的是『人』,不在於地方。有些人雖然嫁在老家附近,不探望,照樣的不探望。女婿真是有孝心的,千里萬里一樣隔不住人。人常說:親親故故遠來香,嫁得愈遠,心越是貼近,難道不好?!……」她頓一頓,又說:「這些道理,我卻不能一口氣對她去說,我這做晚輩的,怎好拿道理反去教訓尊長?」
「我說過,妳認為慢慢來,是絕對對的。」葛德說:「她意識就是那樣,有什麼辦法呢?也許過一段日子,她對我有了瞭解,情形就會轉變了,沒有什麼樣的因素使我不能等的。」
「其實,她的心地真是寬和善良。」女孩兩眼泛溼說:「我在告訴她我們相處的事之後,從她眼神裏,我看出她驚愕,不很贊同,她曾動了幾次嘴唇,但都沒有把反對的話說出口來,……她是怕我傷心。這不是習俗、規矩和制度的問題,這是做人免不了的情感的牽掛。」
「不要為這事再煩心了,碧霞。」葛德緩語溫聲的湊近她的臉說:「打今天朝後去,妳還是專心忙妳的功課罷,妳已經耽誤掉不少的時間了。」
「對啦,」女孩忽然想起什麼來說:「既然我們要等下去,我原先住的地方,離這邊實在太遠了一點,你不妨替我留意著,這附近要有房間出租,適宜單身女性居住的,不妨跟房東談談,幫忙替我租一間。我目前沒做差事,我母親知道之後,給我一筆生活費,包括房租錢。我在那邊兩人合住,雖說省一些,但同房的她做事,夜晚我看書會影響她睡覺,儘管她說沒關係,畢竟很不方便。
「是的,」葛德說:「累妳兩頭跑,我老早就覺得很難受,但妳知道,我的經濟能力這樣弱,實在……妳如果能住在附近,當然就方便多了。」
「我也是早就想過的,只是當時沒有提。」
「我想,分租的房間比較容易找,」葛德說:「雖然平常沒有認真的留意,至少在印象裏,街頭巷尾,貼有很多這樣招租的條子。趕明天,我就出去兜兜圈子,多看幾處地方,選離這兒最近便,環境又很適宜的,而且,價錢又很適合的,……妳是省儉慣了的人。」
「那當然,」女孩轉動黑眼笑說:「能省些錢,多買幾瓶乳白魚肝油,把你餵得略微壯一點點也好,但也不必太壯──太壯就不像一個窮作家了。」
她笑起來,笑得真,笑得有些恣意的奔放,她嬌而脆的笑聲,真像一串搖動的鈴子,鈴聲使他的心跟著搖漾,從這裏,他可以看出她真樸的本性來。他知道,一般出生在農村裏的女孩子,大多懂得收斂,唯有在私底下,和她極熟悉極相知的人相對的時候,才會展露她的真性情,沒有矯飾,沒有浮誇,這是一種活潑的,自然的嬌憨。
「我要阻止妳再講下去了。」他說。
他用粗莽的動作吻了她,把他的思念融在裏面。她接受了,只一忽兒便推開了他,用警示性的語氣說:「葛,我不反對親熱,但還是讓我們適可而止罷……人在平常總很自信,當感情泛濫的時候,你知道,我很駭怕……。」
「抱歉,碧霞,」葛德退到椅上坐下來低聲說:「我無意驚嚇妳,我只是告訴妳,妳南下這許多天。我實在很想念妳,妳走後,我生活裏彷彿缺少了什麼。」
「我還不是一樣,」女孩掠掠頭髮說:「陪我母親,困守在病房裏這些天,情緒很不好,白天夜晚都有些昏昏沉沉的,我總想到你是不是是吃了冷飯?是不是吃飽了?想到你是不是深夜還在熬著寫稿?……有時我在笑自己,怎麼會變得這樣瑣碎了?!我又想到,我們都像是蜘蛛,總坐在感情的網裏。」
「多適當的比方!」葛德說:「妳是純情的,我只能說是惜情,我總愛朝玄處想,對我來說,獲得這份情感,真是太難了。妳到南部去後,我常常一個人在呆想,以為這不是真的,只是一場夢。」
「那準是你平常寫多了,想多了,神經有些過敏了。」女孩說:「其實在真正的生活裏面,人與人產生情感,太平常啦。你早年的那些朋友,不都是一個一個的築起他們窩巢了嗎?……我從沒把它當成夢看過。」
「其實,有這種疑真似幻的感覺也很好,」葛德品味著他自己的話說:「這樣,當我發現它不是夢的時候,便更加珍惜這份情緣了。」
「你能有這樣的想法,真使我感動,葛!」女孩說:「我只是一個很平常的鄉下人,我能帶給你的,並不比別人多,日後,做家務,帶孩子,換了旁人,一樣會做的,如果硬說多點別的,那就是我渴望你能安心寫作,能留下一些好的作品,……我相信你能寫出更好的作品來的。」
「有了這些,我還能多要什麼呢?」葛德說:「秦牧野早先提到過,就他的看法,好夫妻有三種,一種是心靈契合的,彼此談得來,情感深厚,又知心。一種是個性適合,相忍相讓,平淡裏帶點兒甜味,但在精神境界上,略有參差。一種是情感好,各盡分份。我覺得,妳該算是第一等的。」
「虧你老面皮,」女孩走過去,用指甲輕觸他的臉說:「你說的不羞,我聽的卻羞得慌呢!」
「我們言歸正傳罷,」葛德說:「我明天就去替妳在附近找間房子,找妥了,儘快搬來,省得每天來往奔波。一等搬定了,妳就專心準備妳的功課,有許多雜務事情,讓我來料理,……活動活動筋骨也是好的。妳今天一路坐車勞累,該早些回去休息了,我下逐客令啦!」
葛德這回辦起事來,真的很認真。第二天,出門跑了半天,一共找到三家比較適宜的出租的房子,前兩處是公寓分租的房間,後一處是蓋在一家人家後院的小磚屋,一房一廳帶廚廁的,如果從後門進入,就變成單家獨院的小型平房住宅,租金略微高些。葛德和女孩商量,黃碧霞毫不猶疑的選了後一處地方。
「好是好,只是有些不合經濟原則,」葛德說:「租金實在貴了一點。」
「真的貴嗎?」女孩說:「日後我們結了婚,不必再去費心找房子了,只要把小木樓退租就成了,我是這樣打算的。」
「妳真是有打算,我可沒想到這一層。」葛德說:「不知妳想到沒有?萬一好事多磨呢?」
「那也沒什麼,」女孩說:「我住到考完,如果能考進學校,我會找幾個女同學來合住,負擔自然就減輕了。我總覺得,單獨進出的房子,要比跟房東處在一起方便得多,這種房子找起來很難的。」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葛德陪黃碧霞一道去看房子,簽妥合約,很快就搬了過來。那家的後院很大,至少有廿多坪,中間鋪上水泥通道,兩旁是荒蕪的花圃,叢生著雜草,雜草叢中,還有一枝憔悴的玫瑰探出來,但沒有發花,在牆角,有一棵久沒修剪的老榕,還有一棵棕櫚,具有些庭園的趣味。
房子蓋得比較簡單,單磚灰瓦,由於年月比較久,房子空著沒人住,只儲藏了一些廢棄的雜物,因此顯得有些陰溼,窗臺和牆壁上,生了不少的黴斑,但這不算什麼,只要略作打掃,開開窗子除除黴氣就好了。
葛德和女孩兩個,花費了兩天的時間,整頓這所小房子,把她的新住處,安頓成一個環境幽雅,几淨窗明的地方,很適合安心複習功課。
也許很久沒作過這樣的體力勞動,女孩還好,葛德累得只是搥腿搥腰。
「真抱歉,把你累成這樣。」女孩說。
「不要緊,」葛德說:「回去燒水洗把澡,休息一兩天就會復元了!雖然勞累一點,但我心裏卻很高興,因為不必擔心妳再頂風冒雨的跑來跑去了!」
「我們能租到這房子,真不容易,離小木樓只隔兩條巷子。」女孩說:「你那邊沒有廚房,臨時煮飯,弄得滿屋子油煙,我看,不如把它移過這邊來,到時候,你走幾步過來用飯,更適合一些。」
「碧霞,」葛德有感於衷的說:「這樣,越來越像一個小家庭了,我真怕有一天我要是失去它,我一個人更沒有勇氣去飄泊啦。」
「你想你會失去它嗎?」女孩說:「我真願發誓,我在世上活一天,我就會堅持到底的。」
「我當然感激妳這種堅持,」葛德說:「不過,妳要瞭解,有時候,一個人的能力很有限,如果過分堅持,就會釀成悲劇的,我不忍也不願眼見那種結果。」
「也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女孩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有感情的基礎,沒有什麼外力能撼得動它,你看我們像是那種悲壯的人物嗎?……我堅持,主要是保有自己選擇幸福的權利。我並不是傻子,不是嗎?」
事實上,葛德不能不默認他早已沉浸在幸福的感覺裏面了。有了這樣一棟安適的小屋,一個綠蔭遮掩的小小庭園,他和她耳鬢廝磨的相守著,談詩、論文、寫夢,然後,女孩準備她的課業,他回到小木樓上去寫稿,各人努力於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捨棄了這些,他還能求取旁的什麼呢?這生活曾經是仰企不及的夢境。
女孩提議平常盡可忙碌,但週末和星期假日,還是要輕鬆下來,做些有益身心的活動,像登山和郊遊什麼的,她說:
「我看過好幾位有名的作家,有的患有酒癖,雖然常自居飲者,其實已經算是酒徒了;也有的過於勞心,瘦得一把骨頭,一走動就氣喘吁吁的,充分顯出未老先衰的徵兆;也有的懶得運動,渾身肥肉,像一隻吹鼓了的氣球。我可不願見你變得和他們一樣,你有沒有注意過,你的腰已經有些駝了,全是坐出來的。」
「但妳要我爬山,我怕是爬不動了!」葛德說:「我是不會做登山協會會員的,他們一瞧著我這副模樣,絕對不肯要我。」
「我又沒勉強你去攀登三尖五怪那種大山,」女孩說:「像郊區的七星、大屯、拇指山之類的小山,任是誰都能爬的。人到綠林裏,精神像洗過一次澡樣的清爽。你開始時,也許會覺得有些疲累,慢慢就會習慣了!」
「只要妳堅持,我就願意盡力去嘗試了!」葛德說:「先從郊遊散步開始,逐漸爬一點小山,我想累是可能累一點兒,也累不到哪裏去的。」
女孩很認真的計畫著去哪些地方,看花,聽泉,或是尋覓幽境。她所列出的郊區多處地方,葛德都曾經多次去過。一般說來,越是所謂郊區名勝風景,越是顯得沒有味道,有人形容那些地方本來並不壞,但都被人玩渾了,到處是土產店,小吃攤,瓜皮果屑和遍地垃圾,反而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還能保持一份原始的清幽。不過,當他眼她在一起時,便覺得平常認為毫不足取的地方,風景也都變美了。他們牽著手,走到離開人群較遠的地方,或是坐著察看野花草,或是彼此不說話,諦聽微風搖落松實的聲音,這時候,他們便敏感的觸及到季節的變化,並深深的融入了自然。
情感可以美化風景,他真的這樣想過。
他和她到情人廟去膜拜過,他們分別的許過願,她調皮的問他許的是什麼樣的心願?葛德深深的凝視著她說:
「碧霞,我記得我有個老班長,他老家住在黃河岸邊,抗戰時入伍當兵,輾轉到過很多地方,當他隨著隊伍在米脂剿共時,當地盛產大棗、他吃了棗子,卻把一枚棗核留在身上,有人問他留棗核幹什麼?他說將來承平了,要帶回老家去種植,讓它開花結果。……他能帶棗子,我能帶人。我祈求有一天,兩岸承平了,我能把妳帶回我的家鄉去。」
「我會等的,那何嘗不是我的心願?」女孩說:「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帶你到這兒來麼?當初卓文君跟司馬相如離家,也過過很窮的日子,我一樣願意跟你過窮日子,你帶我到天涯海角,我都會去的。」
「我記得這座廟初建時,有很多人議論過它,認為建造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塑像供人膜拜,不妥當。誰知道也有許多人熱愛他們,至少,他們真正懂得愛情。」
「其實,板著面孔衛道,大可不必。」女孩說:「願意拜的自會來拜,不喜歡他們的,就不來好了。在鄉下的許多廟裏,以人為廟的也很多,何況相如是個文學家,為什麼不讓後世人景仰呢?」
「也許是社會習俗的關係罷。」葛德說:「在丹麥,安徒生忌辰的夜晚,仍有許多孩子們為他提燈;在英國,人們對於莎翁極為尊敬;我們當代也許還沒有那樣的作家,至少李白杜甫也該有座廟罷?如果有,我是贊成的。」
「你忘了,我們在端午,不是也紀念屈原嗎?」
「孩子們和一般人,誰知道屈原?誰讀過他的作品?誰瞭解他的精神和他的為人?」葛德有些激動起來:「大家都只知道吃粽子罷了。」
另一個週末,葛德提議去指南宮,女孩搖頭拒絕,她認真的說:
「並不是我迷信那些流言和傳說,這是一個人心理上的問題。傳說如果一對情人去參拜呂祖廟,他們結果都是勞燕分飛的多。討吉利的心理,是誰都有的,我們何必自己去觸自己的霉頭?再說,可去的地方正多,並不一定非到那兒不可,我們找一處野溪,看流水看石頭也是好的。」
他們真的去找野溪了。在石碇鄉用午飯,沿溪走著,因為離熱天還有一段日子,撲面的春風仍略帶寒意。女孩談起上一年的夏天,她曾經和女友做伴,來過這裏,在溪心嬉水,捕蝦,用一面鐵絲絡子,張在石頭砌成的野灶上,自己燃火烤肉。她說起夏季來時,這溪岸的鬱勃,林子裏,飛著無數螢火,黃昏時,滿耳都是蟬鳴的聲音。有許多輕便的帳篷,搭在河邊平坦的石臺上,露營的年輕人,嬉笑著,對著月光,放聲的唱歌……。
「但我還是喜歡現在這樣子,只有我們兩個人。」葛德說:「唯有安靜,才能使人體會到自然的美。」
「其實,在我們鄉下,這樣的地方隨處都有。」女孩說:「人住在城裏,好像籠鳥,望著籠外的天和地,明明很平常,也以為是很美了!無論如何,它使你感到心境和朗寬鬆,這卻是真的,尤其是對寫作用腦的人,有意想不到的效用,這就是我逼你出來的理由!」
女孩所說的話,葛德早已感覺到了。他半生從來沒有過過這種感情溫潤的日子,它像是一首平靜的,帶有夢意的歌,它安撫他的早先的困頓、焦灼和起伏無定的鬱躁。他曾經想過,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面對著生活時,應該感受生活浪潮的直接衝擊,但必須要有個適於寫作的環境,推展開一顆平靜的心,才能反芻精神的蘊蓄,把它吐放到紙上,成為作品。他早些年寫不出稿子來的原因,現在終於被自己發現了,那是他心情始終沒得平靜。他更從這裏領悟到,不論是怎樣剛強的人,總不能常年累月的吶喊著,憑藉他的性格和單一的勇氣,直衝而前,他總得要有屬於個人的感情生活,便他的勇氣得到培養。
他更發現,精神上的釋放和付出,都只是概念性的,有時根本不切實際;一個人依著概念去釋放自己,展得太寬,放得太廣了,精神質素便自然的變得稀薄起來,而且,沒有特定的對象可以投射,它們便飛浮起來,如浮雲片羽,飄忽游離,全無落處。如今就不同了,他愛著黃碧霞,對於她的一切,他都得懇實的付出他的關心,他得體會對方的心情,瞭解對方的心理,不論在實際生活或精神生活上,他都要進入她的世界,探索到細處、隱處、微處,這是一種責任。
他記得死去的彭東,會經拿藝術作比方,用之證映人生,他說:「有些從事抽象繪畫的大師,從眼見的現實世界逐漸抽離,昇華到心靈世界裏去,展現無形之境,但,人活在世界上,生活的根鬚仍然深紮在現實當中,人總難以抗拒生活的直接影響。他們抽離到某種程度,便要回顧現實,從而覓求本身的定位。否則,便飄飄盪盪的凌入虛空,覓不著自己了。」彭東很贊成這種藝術回顧的論點,對於一些著名的抽象畫家,每一年總要認真畫幾幅具象作品的舉動,認為是著重根本的現象。
他當時聽了這段話,只能說略有感觸,也曾把它記在札記,但並沒有深沉的思索它,從其中體悟出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如今,他才真正領悟,人生也正如此的。
他早先空抱著救世拯難的文學心胸,寫呀,寫呀,自己點燃著自己,他實際上只是囚在小木樓上的,一個又貧窮又潦倒的單身漢,一個和廣大社會生活並不融和的、神經質的人物,他對外間,除了感情的繫念,一切都陌生茫然;沒有透視,哪有認知?……人在概念裏,總會使自己本身的形象變得膨脹起來,彷彿很巍峨的樣子,而那只是不切實際的自我幻覺罷了。……這和抽象的意味差不多,廣而不透、浮而不實很容易不自覺的形成。
他現在該是回頭現實了,不求陳義太高,只要以一個平凡的人的立場,抱一種平凡的心志,在現實生活裏,學習著實際愛人,關心人;有了這種基礎,再求逐步擴大,這就是先具象而後抽象。
他是一隻在黑夜裏盲飛亂撞過的傷鳥。
如今,他應該在這塊小天小地當中暫作休憩,療養他的傷痕,生出他的新羽,這樣,他才能具有充分的,長途飛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