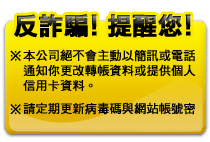◎【第一卷】思想起
*祖先崇拜
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又於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原人思想,以為萬物都有靈的,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存留於世上,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否則便要觸怒死鬼,發生災禍,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
現在科學昌明,早知道世上無鬼,這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了。這宗風俗,令人廢時光,費錢財,很是有損,而且因為接香煙吃羹飯的迷信,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謬說,買妾蓄婢,敗壞人倫,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為高上的理由,是說「報本返始」,他們說,「你試思身從何來?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極之恩,你哪可不報答他?」我想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兒子,在兒子並沒有什麼恩,在父母反是一筆債。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
在自然律上面,的確是祖先為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們(父母)的義務開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稱孝順的兒子是還債的,但據我想,兒子無一不是討債的,父母倒是還債——生他的債——的人。
待到債務清了,本來已是「兩訖」;但究竟是一體的關係,有天性之愛,互相聯繫住,所以發生一種終身的親善的情誼。至於恩這一個字,實是無從說起,倘說真是體會自然的規律,要報生我者的恩,那便應該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實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於子女的債務——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當辦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盤古時代以至類人猿時代,這樣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決不可許的了。
我最厭聽許多人說,「我國開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麼樣」。開化的早,或古時有過一點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樣崇拜,彷彿人的一生事業,除恭維我祖先之外,別無一事似的。譬如我們走路,目的是在前進。過去的這幾步,原是我們前進的始基,但總不必站住了,回過頭去,指點著說好,反誤了前進的正事。因為再走幾步,還有更好的正在前頭呢!
有了古時的文化,才有現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們。但倘如古時文化永遠不變,祖先永遠存在,那便不能有現在的文化和我們了。所以我們所感謝的,正因為古時文化來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夠留下現在的文化和我們——現在的文化,將來也是來了又去,我們也是生了又死,能夠留下比現時更好的文化和比我們更好的人。
我們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孫崇拜我們。
尼采說,「你們不要愛祖先的國,應該愛你們子孫的國。……你們應該將你們的子孫,來補救你們自己為祖先的子孫的不幸。你們應該這樣救濟一切的過去。」所以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為自己崇拜——子孫崇拜。(八年三月)
*思想革命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運動漸見功效,除了幾個講「綱常名教」的經學家,同做「鴛鴦瓦冷」的詩餘家以外,頗有人認為正當,在雜誌及報章上面,常常看見用白話做的文章,白話在社會上的勢力日見盛大,這是很可樂觀的事。
但我想文學這事物本合文字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麼用處呢?
我們反對古文,大半原為他晦澀難解,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使得表現力與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別一方面,實又因為他內中的思想荒謬,於人有害的緣故。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間,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沒有經過廓清,所以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為一,不能分離。
我們隨手翻開古文一看,大抵總有一種荒謬思想出現。便是現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幾個古典熟語,那種荒謬思想已經滲進了文字裡面去了,自然也隨處出現。譬如署年月,因為民國的名稱不古,寫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黨氣味,寫作「己未孟春」,又像遺老。如今廢去古文,將這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但他們心裡的思想,恐怕終於不能一時變過,將來老癮發時,仍舊胡說亂道的寫了出來,不過從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話罷了。話雖容易懂了,思想卻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好比「君師主義」的人,穿上洋服,掛上維新的招牌,難道就能說實行民主政治?這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
中國懷著荒謬思想的人,雖然平時發表他的荒謬思想,必用所謂古文,不用白話,但他們嘴裡原是無一不說白話的。所以如白話通行,而荒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樂觀,因為他們用從前做過《聖諭廣訓直解》的辦法,也可以用了支離的白話來講古怪的綱常名教。
他們還講三綱,卻叫做「三條索子」,說「老子是兒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講復辟,卻叫做「皇帝回任」。我們豈能因他們所說是白話,比那四六調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話文,和一篇「非復辟」的古文並放在一處,我們說那邊好呢?
我見中國許多淫書都用白話,因此想到白話前途的危險。中國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就是改學了德文或世界語,也未嘗不可以拿來做「黑幕」,講忠孝節烈,發表他們的荒謬思想。倘若換湯不換藥,單將白話換出古文,那便如上海書店的譯《白話論語》,還不如不做的好。因為從前的荒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澀的古文中間,看了中毒的人,還是少數,若變成白話,便通行更廣,流毒無窮了。
所以我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於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閒卻了這一面的重大問題。(八年三月)
*前門遇馬隊記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時後,我從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門買點什物。走到宗人府夾道,看見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覺得有點古怪。到了員警廳前面,兩旁的步道都擠滿了,馬路中間立站許多軍警。再往前看,見有幾隊穿長衫的少年,每隊裡有一張國旗,站在街心,周圍也都是軍警。我還想上前,就被幾個兵攔住。
人家提起兵來,便覺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樣的中國人,有什麼可怕呢?那幾位兵士果然很和氣,說請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對他說,「那班人都是我們中國的公民,又沒有拿著武器,我走過去有什麼危險呢?」他說,「你別要見怪,我們也是沒法,請你略候一候,就可以過去了。」我聽了也便安心站著,卻不料忽聽得一聲怪叫,說道什麼「往北走!」後面就是一陣鐵蹄聲,我彷彿見我的右肩旁邊,撞到了一個黃的馬頭。
那時大家發了慌,一齊向北直奔,後面還聽得一陣馬蹄聲和怪叫。等到覺得危險已過,立定看時,已經在「履中」兩個字的牌樓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計算出前門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須得向那裡走才免得被馬隊衝散。於是便去請教那站崗的員警,他很和善的指導我,教我從天安門往南走,穿過中華門,可以安全出去。我謝了他,便照他指導的走去,果然毫無危險。
我在甬道上走著,一面想著,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確是本國人的樣子,只有那一隊馬煞是可怕。那馬是無知的畜生,他自然直衝過來,不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法律。但我彷彿記得那馬上似乎也騎著人,當然是個兵士或員警了。那些人雖然騎在馬上,也應該還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憑馬匹來踐踏我們自己的人呢?
我當時理應不要逃走,該去和馬上的「人」說話,諒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夠保護我們。我很懊悔沒有這樣做,被馬嚇慌了,只顧逃命,把我衣袋裡的十幾個銅元都掉了。
想到這裡,不覺已經到了天安門外第三十九個帳篷的面前,要再回過去和他們說,也來不及了。
晚上坐在家裡,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氣又喜。氣的是自己沒用,不和騎馬的人說話;喜的是僥倖沒有被馬踏壞,也是一件幸事。於是提起筆來,寫這一篇,做個紀念。
從前中國文人遇到一番危險,事後往往做一篇「思痛記」或「虎口餘生記」之類。我這一回雖然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卻是初次。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過兵警的呵叱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如今在本國的首都,卻吃了這一大驚嚇,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驚小怪,寫了這許多話。可是我決不悔此一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